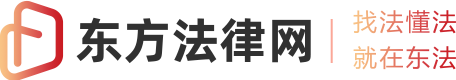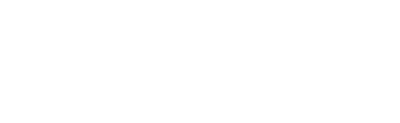我國《民法通則》人身監護責任的缺失與完善
- 期刊名稱:《法律適用》
我國《民法通則》人身監護責任的缺失與完善
Defects and Improvement of Guardianship System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in China
監護乃督察、督管和監督保護。作為一項民事法律制度,監護是依法對未成年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進行監督、保護的制度。鑒于未成年人的年齡、智力發展狀況,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不能自我保護民事權益,不能獨立實施法律行為以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我國現行《民法通則》在學界的“監護權利說”和“監護職責說”中確認了后者,使得監護這項古老而又年輕的法律制度。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十分獨特的功能和價值。然而,我國《民法通則》有關人身監護責任的規定尚存諸多立法缺陷,致使司法活動無法可依的情況亟待改變。以下筆者試圖對我國《民法通則》人身監護責任的缺失與完善作出探討。
一、民事審判中確定人身監護責任的司法困惑
(以下案例當事人為化名)原告曾瓊與被告一柳棗婚后于2003年6月9日育一女柳珍。2005年1月,曾瓊與柳棗因夫妻感情不和,經法院訴訟調解自愿達成離婚協議。女兒由柳棗撫養,曾瓊每月給付撫養費150元。后柳棗與被告二黎湄結婚,于2006年2月搬到黎湄所有的某區湄莊11—7號房屋(系該棟房屋頂層)居住。次月某日14時許,黎湄外出,柳棗陪柳珍玩耍一會兒后便在客廳上網。稍許,黎湄新雇保姆敲門,柳棗不見柳珍便立即尋找,后在所住樓房右側底下一條小溝里發現柳珍。柳棗立即將柳珍送往急救中心,經醫院診斷柳珍已經死亡。公安機關勘查認定:柳珍系意外高墜死亡。另查明,黎湄房頂女兒墻高81公分。2001年8月,黎湄與前夫在該女兒墻根做花臺高44公分,女兒墻上端未設防護欄。黎湄家有一樓梯,可直接從屋內通往樓頂,柳棗尋找柳珍時發現屋內直通樓頂的房門開啟。
原告曾瓊訴稱,黎湄所有的屋頂女兒墻未設防護欄.致柳珍跌落摔死。柳棗對柳珍監護失控,黎湄對自家屋頂存在明顯的安全隱患視而不見,致柳珍死亡。請求判令二被告支付死亡賠償金92210元(按200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21元計算20年,以原告應享有的一半主張)、精神撫慰金3萬元。被告柳棗辯稱,柳珍死因已經公安機關查明系意外事故,本人無過錯,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黎湄辯稱,對柳珍的死亡無法預見,無任何過錯,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對本案的處理形成三種觀點,分別是全面賠償論、適當賠償論和不予賠償論。
全面賠償論認為:二被告對被監護人監護不力,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原告關于女兒死亡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均應支持。原因如下。
首先,被告一承擔監護不力民事責任的理由在于: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包括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為被監護人提供安全的生活環境,保護被監護人身體健康等。監護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應當對未滿3歲的小孩實行全天候監護。被監護人尚無民事行為能力.不可能認識到自己爬上樓頂上的花臺、繼而又爬上女兒墻存在危險。由于被告二屋頂花臺上端距女兒墻頂部僅37公分,女兒墻上端未設置防護欄,存在嚴重安全隱患,二被告未采取防范措施。被告一應當預見被監護人獨自一人在屋頂玩耍可能會發生的危險,卻疏忽看管照顧。被告二承擔監護責任的理由在于:監護人是具體執行監護職責的人。監護制度是為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合法權益而設置的一項民事法律制度.是對行為能力欠缺的一種救濟。監護不力給被監護人造成損害,理論上仍然應當歸結為不作為的侵權責任。二被告結婚后,被監護人與其共同生活,被告二與被監護人形成有扶養關系的繼母女關系,是監護人之一。被監護人高墜事故發生前。被告二外出時沒有履行提醒義務,沒有采取給屋頂門上鎖等安全措施,其在被監護人發生事故時不在家的事實,不能成為監護責任的免除事由。
其次,“以人為本”是我國的立法傾向。人死不能復生.生命權是人最寶貴、最終極的權利,生命的喪失是對人生權利的毀滅性破壞,在道義上應當給予最嚴厲的譴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9條規定的死亡賠償金,采取的是撫養、繼承喪失說,即死亡賠償金被界定為賠償義務人對受害人之法定繼承人。因受害人死亡而遭受的未來可繼承的受害人收入損害的賠償責任,在計算死亡賠償金時,以受害人家庭整體減少的收入為標準,即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標準進行計算。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第18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等相關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獨立成訴非常明確,致人死亡,特別是致親生兒女死亡,權利人以遭受精神損害為由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其請求。
適當賠償論認為:原告的訴訟請求只能適當予以主張。理由是,原告與被告一離婚后,被告一撫養被監護人,原告僅承擔150元/月的撫養費。相比之下,被告一履行了較多的撫養義務。被告二作為繼母,也已盡力所能及的監護義務。如果嚴格按照死亡賠償金的規定主張,顯失公平。
不予賠償論認為:二被告因監護不力致被監護人死亡而對作為被監護人生母的原告承擔賠償責任沒有法律規定;該案涉及親權關系,不同于一般侵權賠償。故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本案提出了一個立法尚無規定且尚未引起人們注意的司法困惑:監護人在履職中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是否對被監護人的生父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另外.建筑物因管理不當致人死亡,該建筑物的管理責任與監護責任能否競合?
二、《民法通則》人身監護責任立法缺失的原因
19世紀前,全世界對兒童的認識十分落后,兒童僅僅被看成是一種所有物,主要以經濟價值來衡量,完全附屬于父母。[1]至20世紀下半葉,聯合國大會1990年9月正式批準生效的《兒童權利公約》對各國監護制度的立法、司法產生空前影響。兒童才被逐步賦予法律人格,成為法律權利的擁有者和行使者。
具體到我國,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影響,加之我國市場經濟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立法、司法理念嚴重不適應現代化建設發展需要。主要表現在現行人身監護職責重私力自救、輕公力干預。重財產監護、輕人身監護的傾向。未成年人尚處在“家庭人”、“親屬人”的偏狹私域。“國家人”、“社會人”的現代身份尚待確立。由此導致不少地方,家庭被視為私有領地,子女被視為家長的私人財產.即使監護人嚴重失職,甚至嚴重侵犯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知情者也司空見慣,國家立法、司法似乎鞭長莫及。
監護行為的利他性、職責性決定了監護制度的強制性。然而,《民法通則》規定的關于監護制度的四條基本原則、《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以及其他有關人身監護制度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均缺乏可操作性,對監護人侵犯被監護人人身權利的情形,從“假定、處理、制裁”等規范結構上,至今還難以找到充分的法律依據。
三、《民法通則》人身監護適用全面賠償責任的法理思考
監護關系并有私法及公法的性質。[2]監護制度自羅馬法起源至今,已經從一種以宗族制和家長制為基礎的“支配權”,演變為一種以立法公法化、社會化為基礎的一種“保護被監護人利益的社會公益性職責”。[3]此種立法及司法走向決定了我國《民法通則》人身監護應當適用全面賠償責任。
(一)民事權利法律保護系人身監護全面賠償責任的法律原則
《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2條提出,“民事權利受法律保護,非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并根據合法程序。不得予以限制。”該建議稿認為,法律保護民事權利是基本原則,只有當民事權利的法定限制條件同時具備時才能例外;民事權利的法定限制條件只對財產權利有效,對人身權利,民法不能規定任何限制條件。[4]這就從理論上可以推導出人身監護全面賠償責任的命題。自然,相對于監護人是全面賠償責任,相對于司法活動是全面賠償原則。全面賠償責任是指侵權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的大小,應當以其行為造成的實際的財產損失大小為依據,全部予以賠償。換言之,賠償范圍以所造成的實際損失為限,損失多少,賠償多少。全面賠償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是現有財產的減少;間接損失是可得利益的喪失。
(二)請求權競合與固有侵害說原理系人身監護全面賠償責任的法理依據
在法律上,競合是指某種法律事實的出現,導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權利產生、各項權利相互沖突的現象。[5]用民法大師史尚寬的話說,就是依同一法律事實,于同一當事人間具備兩個以上的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兩個以上之請求權之狀態,謂之請求權之并存或競合。[6]請求權競合是指基于一個法律事實產生數個請求權,該數個請求權的救濟目的相同,但是數個請求權的內容相互沖突,只能選擇其中一個請求權行使的請求權并和現象。[7]請求權相互影響說認為,在請求權競合的情況下,當事人只可以主張一個請求權,不得重復或者同時主張復數的請求權。但是,為克服不同請求權在管轄法院、訴訟時效、證明負擔、證明標準、賠償范圍等方面的差異給原告帶來的不便和不公,允許不同的請求權之間相互影響。在主張侵權法上的請求權時,可以適用契約法上的有關規定,依此類推。[8]由請求權競合說推導,建筑物因管理不當致人死亡,該建筑物的管理責任與監護人在履職中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的人身監護責任引起的侵權請求權可以競合,當事人可以選擇其中之一請求權行使。
監護人在履職中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必然涉及死亡賠償金的適用。死亡賠償金是指在受害人因遭受人身傷害失去生命的情形下。由賠償義務人給予其家屬一定的賠償費用。它首先應當界定為財產損害而非精神損害賠償,亦即它已不是以前司法實務所謂的精神損害賠償,而是財產損害賠償的一種。[9]固有侵害說認為,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近親屬的賠償,而非對死者的賠償。基于死者與其近親屬密切的生活聯系,對生命權的侵害,必定意味著近親屬生活利益及扶養利益的喪失,此種利益屬于近親屬固有的利益。出于維護社會利益的考慮,有必要為受害人近親屬提供補救。受害人近親屬享有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依據不是受害人的生命權,而主要是受害人與其近親屬的血緣關系。這種血緣關系是一種社會化了的血緣關系,被賦予了社會調控的使命。所以,基于它的補救不是對權利的補救,而是民法出于社會目的對這種關系意外斷裂的補救。說觀點被以法律形式予以確認的包括除葡萄牙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近親屬遭受固有侵害的賠償計算有兩種學說。第一種扶養喪失說認為,由于受害人死亡導致其身前依法定扶養義務供給生活費的被扶養人因此喪失了生活來源,這種損害應當由賠償義務人加以賠償。其賠償范圍是:被扶養人在受害人生前從其收入中或者有權獲得的自己撫養費的份額。目前采此說的是德國、英國、俄國和美國大多數州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二種,繼承喪失說認為,受害人倘若沒有遭受損害,在未來將不斷地獲得收入.而這些收入本來是可以作為受害人的財產為其法定繼承人所繼承的。但因加害人的侵害行為導致受害人死亡,使得受害人無法獲得這些本來應該獲得收入的喪失,從而使得受害人的繼承人也無法獲得這部分應得的利益。因此.因受害人死亡而喪失的未來可得利益,義務人應當予以賠償。[10]
(三)可資借鑒的域外司法經驗
1975年10月4日下午,當事人James Nuessle帶其3歲兒子Michael Nuessel到雜貨店購物。James進入藥房10至15秒后,突然發現兒子不在身邊,便四處找尋Michael的下落。當James透過店內的玻璃看到兒子跟隨一陌生人穿越Grand Avenne.便立刻沖出店外,當街呼喊兒子的小名“Micker”。當Michael發現父親的呼叫,又越過Grand Averme準備回到父親處時。卻被汽車撞個正著,身受重傷。于是。兒子向父親James提起訴訟,要求承擔“管教失當”之損害賠償責任。父親則抗辯法院應以立即判決(Summary Judgement)從程序上駁回原告之訴,蓋被告享有“父母豁免原則”(Parental Immunity)之適用。地方法院同意被告之抗辯,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上訴。二審法院判決發回更審。理由是.法院僅當保留兩種例外情形,使父母豁免原則在合乎要件的情形下可以被告所主張.而達到豁免之目的:第一。當父母的行為系出于“合理的行使監護權”(Reasonable Parental Authority)時。第二,父母的行為系為子女提供衣食住行、醫療等基本生活需求,基于其己身之生活經驗所最出之“一般性的裁量”(Ordinary Parental Discretion)時。同時認為,下級法院援引父母豁免原則而駁回原告之訴,系屬無理,被告上訴有理由,原判決應予以廢除,發回更審。“父母豁免原則”制度自此不再被援用。[11]
四、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人身權利的法律屬性
以上述案件為例,作為被監護人的未成年人,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其對自身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的保護能力十分欠缺,需要有監護人加以保護。使其免受不法侵害。正因為如此,我國《民法通則》借鑒德國、法國、瑞士等國的立法經驗,于第18條規定: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亦有類似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0條規定,監護人的監護職責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管理和保護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理被監護人進行民事活動.對被監護人進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監護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者與他人發生爭議時,代理其進行訴訟。其中,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被監護人的生活被放到首位,其重要性涇渭分明。第20條規定,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了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民法通則》第16條、第17條規定的其他有監護資格的人或者單位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審理;要求變更監護關系的,按照特別程序審理;既要求承擔民事責任,又要求變更監護關系的,分別審理。分析上述規定,不難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被監護人的生父母對其他履職監護人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的,不僅享有訴權,而且享有普通程序保障。
第二,以監護人的行為方式為標準,侵害被監護人人身權利的行為。可分為作為和不作為。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義務而不履行為不作為。如本案對作為幼兒的被監護人不進行基本生活上的照護,導致損害發生。這種因監護人不作為而造成被監護人合法權益損害構成的侵權即為如前所述的不作為侵權。以監護人的主觀狀態為標準,又可分為故意和過失。我國《民法通則》第18條的規定中,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即為過失和故意侵害被監護人人身權利的法定表述。
第三,侵害被監護人人身權行為包括侵害被監護人物質性人格權、精神性人格權、一般人格權、身份權、身體健康權、生命權等。
第四,侵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只有在侵權人的行為符合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受害人能夠舉證并且舉證成立,方能確定。其損害的轉移,是因為侵權人具有可歸責性,亦即在一般侵權行為場合,其可歸責性是過錯;在危險責任場合,其可歸責性是責任人對危險的可控制性或獲利性。監護人的責任以過錯責任為原則,以無過錯責任為補充。過錯責任依《民法通則》第18條第3款規定,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主觀上存在過錯,因此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確定賠償責任,其構成要件有違法行為、損害事實、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和主觀過錯,四者缺一不可。過錯責任原則適用于一般侵權行為,亦即只有在法律有特別規定如特殊侵權行為時.才不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主要依據《民法通則》第126條的規定.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因對其相關安全設施的失控或疏于管理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第五,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其本身就構成侵權行為;監護權是以義務為中心,監護人履職中或日有監護人的身份而侵犯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自然被囊括在監護法律關系中,換言之,當然不能排除在履行監護職責之外。基于被監護人享有被監護的法定權利,監護人不履行監護義務和職責,或者違背這一法定義務與職責,侵害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既是侵權法上的義務違反,又是親屬法上的義務違反。
第六,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的主要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賠償損失、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
五、完善我國民法人身監護全面賠償責任的立法思路
(一)民法人身監護責任的價值取向
1.兒童最大利益優先考慮。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世界的未來、人類的未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一部分第2、3條規定,初步勾勒了兒童利益最大原則的內涵,亦即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不受基于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的身份、活動、所表達的觀點或信仰而加諸的一切形式的歧視或懲罰。關于兒童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締約國應承擔確保兒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護和照料,考慮到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任何對其負有法律責任的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并為此采取一切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2.受害人權益優先保護。隨著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民法越來越注重對公平正義的維護,更加注重實質正義.更加注重對弱者的保護。在侵權法領域,諸如過錯客觀化、過錯推定或嚴格責任、公平責任等,都是基于“受害者往往是弱者”的基本認識。被監護人是人類最大的弱者,充分體現“優先保護受害人”,其法律價值理所當然。[12]
3.家庭成員權利平等。《聯合國憲章》宣稱,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體現在我國憲法中則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二)國外民法對完善我國民法人身監護全面賠償責任的啟迪
因監護人的故意或過失導致被監護人損害時,監護人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是各國監護法公認的原則。
1.過錯責任和連帶責任立法例。《德國民法典》第1833條規定監護人的責任:(1)監護人有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的,就因違反義務而發生的損害向被監護人負責任。監護監督人亦同。(2)二人以上一同就損害負責任的,作為連帶債務人負責任。[13]
2.善良父母注意義務立法例。《意大利民法典》第382條規定監護人和監護監督人的責任:監護人在管理未成年人財產時應當盡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監護人對因違背監護義務給未成年人造成的所有損失承擔責任。[14]
綜上。我國民法人身監護責任制度,在現行立法基礎上,應當充實以下內容。1.家庭成員享有法律權利平等。2.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以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的一切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活動,均應以“兒童最大利益優先考慮”為原則。3.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應當盡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4.父親、母親及其他任何親屬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履行監護職責中,因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侵害被監護人的人身權益,或者導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的,其法律責任一律不得豁免。5.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履行監護職責中,因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侵害被監護人的人身權益,或.者導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的.應當根據違反義務所發生的損害程度,向被監護人、其他權利人承擔民事責任。兩人以上監護人共同履行監護職責有過錯的。承擔連帶民事責任。6.建筑物因管理不當致人死亡.該建筑物的管理責任與監護人在履職中致被監護人非正常死亡的人身監護責任引起侵權請求權競合的,當事人可以選擇其中之一請求權行使。7.人身監護民事責任,實行全面賠償原則。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
【注釋】
[1]李霞:《監護制度比較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頁。
[2]史尚寬:《親屬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33—734頁。
[3]中國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親屬篇》,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頁。
[4]同上注,第5頁。
[5]王利明、楊立新:《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頁。
[6]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
[7]楊立新:《侵權法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頁。
[8]同上注,第238頁。
[9]同注[7],第649頁。
[10]同注[7],第568頁。
[11]潘維大:《英美侵權行為法案例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頁。
[12]同注[7],第519—521頁。
[13]陳衛佐譯注:《德國民法典》(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頁。
[14]費安玲、丁玫譯:《意大利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