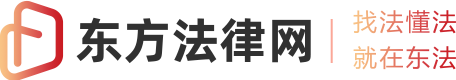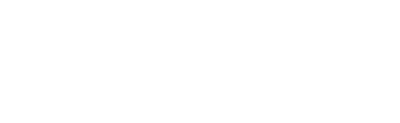論受賄犯罪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
- 期刊名稱:《當代法學》
論受賄犯罪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
【關鍵詞】受賄罪;公務;職務;國家工作人員
On Some Issues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n the Bribe Crime
【英文摘要】For In order to control commercial bribery,it is not only need for attacking accurately,but also request for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to recognize commercial bribe crime correctly.The bribe crime,core of the commercial bribery crime naturally,is very difficult to recognize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such as "meaning of official business","how to judge right benefit "how to process inconsistency in the bribe intention and purpose of securing benefits.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we should focus on two aspects of real practice and ideal condition.
【英文關鍵詞】the bribe crime;official business;duty;country staff
中央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和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都將治理商業賄賂作為今年反腐倡廉的一項重要任務。治理商業賄賂已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在查辦商業賄賂犯罪過程中,無疑要正確認定商業賄賂犯罪,其不僅是準確打擊商業賄賂犯罪之要求,也是保障人權之要求。本文僅就受賄犯罪認定中的幾個問題作一探討,希望能有益于司法實踐。
一、“公務”的認定
就受賄犯罪來說,行為人是否是國家工作人員,是界定受賄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1]的關鍵。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理論界曾有職務說、身份說和公務說。我國刑法明確采用了公務說。所以,是否從事公務又是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標準。
(一)公務的內涵
什么是公務?《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關于國家或集體的事務”。它包括國家性質的公務和集體性質的公務兩大類。國家公務,是指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教、衛生、體育、科技等各個領域中實施的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活動。它具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這里的公共事務范圍較廣,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文體、衛生、科技、以及同社會秩序有關的多種事務的管理。二是具有國家代表性,即這種活動是代表國家進行的,它是一種國家管理性質的行為,這種活動是國家權力的一種體現,或是國家權力機關派生權力的一種體現。而集體公務,則是指集體單位、群眾性組織中的公共事務,它不具有國家權力性。作為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公務”,根據我國刑法第93條的規定,顯然是不包括集體性事務。根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法院紀要》)第一條第四項的規定:“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從這一規定來看,作為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公務”并不限于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在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如果是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同樣是從事公務。所以,公務應從兩方面界定:一是代表性,即必須是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二是管理性,即必須是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如果盡管是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但不是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職責,也不能認定是“從事公務”。
從現有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釋來看,作為界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公務”體現為兩方面:一是國家權力的行使,一是國有資產的管理監督。從應然的角度講,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公務”應該指國家事務,具體地講,僅指國家機關這一塊,不應包括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作為受賄罪,其腐蝕的是國家肌體,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所以,作為受賄罪的主體應該是行使國家權力的人,代表的是國家,當然具體表現為某一國家機關。由于我國市場經濟仍然處于初期,市場秩序沒有完全建立并被遵守,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從保護國有資產的角度看,將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工作人員,對他們的受賄行為從嚴懲處實有必要。某種意義上講,國營企業的運作體現著國家權力的行使,將國營企業的工作人員視為國家工作人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市場經濟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政企分開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只能是國家出資建立的企業,不能把國有企業的財產直接視為國家財產。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在政企嚴格分開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具體運作,如內部管理、對外開展業務(這里不包括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宏觀調控)根本體現不了國家權力的行使。所以,對于國有公司、企業等單位中工作的人員受賄的,應該按照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處理。
(二)“公務”與“勞務”、“職務”的界限
勞務,一般是指直接從事具體的物質生產活動或者勞動服務活動,既可能是體力勞動,也可能是腦力勞動。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將公務與勞務截然對立起來,即認為二者不共存,如果說某人從事的工作是公務,就不可能是勞務。一般來說,公務與勞務是有界限的,公務活動具有國家權力性,勞務則不具有。由于二者性質不同,在表現形式上也有區別:公務表現為組織、領導、監督、管理活動;而勞務則表現為具體的生產活動或服務活動。但是,公務與勞務并非完全對立。在公務中往往也存在著勞務的成分,因為一些公務的履行需要通過勞務來進行,在勞務中有時也含有公務的性質,這主要是指經手國有財產的情況。比如國有公司、企業中的售票員、售貨員,這一直是爭論比較大的。有觀點就認為,從事售貨工作就是勞務活動,但他們在提供勞務的同時,還兼作管理公共財物的工作,以勞務為主,以公務為輔。如果他們利用這一便利條件,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利,就構成受賄。也有觀點認為,應當區分基于管理職能而經管單位財物的人員和基于生產、經營、服務等工作性質而經管單位財物的人員兩種不同情況。前者屬于公務范疇,而后者仍然是勞務的性質。筆者認為,界定公務和勞務,根本的是看這一活動是否具有代表性和管理性,組織、領導、監督職責比較容易界定,管理職責不好認定。管理應包括對人、財、物的管理,對人的管理好認定,對財、物的管理只能是直接的職責,如出納、庫房管理員,但不能是因勞動服務而派生出來的對財、物的管理,比如勞動得有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因勞動而管理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的活動就不能認定為從事公務。
實踐中,爭論比較大的是醫生利用處方權收取回扣的情況。有觀點認為,雖然醫生利用處方權收取回扣是一種受賄行為,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但現行刑法難以涵蓋這一行為,不具有刑事違法性,不構成犯罪。因為醫生開處方的行為,是利用自己的業務技術為社會公眾提供醫療服務,不是“從事公共事務的管理”行為,不具有國家公權力的性質,因而不屬于刑法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也有觀點認為,國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以單位名義所從事的技術性、業務性或服務性工作,是代表國有單位的行為,是國家向社會提供公益活動的有機構成,理應是“從事公務”。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均不妥當。第一種觀點僅僅把醫生的開處方的活動看成是一種單純的業務技術活動,這是不對的。第二種觀點則僅注意到了公務活動的代表性,而未注意到公務活動的管理性。單純的技術服務雖然是代表國有單位向其他人提供的,但由于其不具有管理性,不屬于“公務”。醫生開處方收取回扣,其開處方活動已不是單純的技術服務,因為其開處方行為與醫院的醫藥購銷活動相聯系,醫藥品經營、管理的工作人員正是根據醫生開出的處方來決定采購的數量和品種,醫生的處方行為與醫藥品的購銷行為具有內在、必然的聯系。這樣,醫生的處方權已暗含著醫藥的購銷權,不再是單純的技術服務。也正是此緣故,醫藥廠商才給其回扣。所以,這種情況下,應該認定醫生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當然,如果醫生單純的給病人看病、治病,病人出于感激或其他目的給醫生送錢,則不能認定醫生構成受賄罪。再比如大學教師,如果你單純的教書、改卷,這不是從事公務,但是如果你參與招生,那就是公務了。
所謂“職務”,一般是指職位規定應該擔任的工作。從法律意義上講,職務則意味著獲得一定的法定身份,有權代表國家、集體、社會團體、企業等執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質的事務。在國有單位和非國有單位中均存在著職務,在國有單位,行為人履行職務就是從事公務,而在非國有單位,行為人履行職務,只有在代表國有單位時,才能視為公務。《法院紀要》規定,“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國有公司的董事、經理、監事、會計、出納人員等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等活動,屬于公務。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如售貨員、售票員等所從事的工作,一般不認為是公務。”職權,是指職務范圍以內的權力。從《紀要》規定可以看出,公務與職務具有相連性。
二、受賄故意與謀利目的分離情況的認定處理
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和非法收受型受賄罪,都有一個“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對于“為他人謀取利益”,理論界已達成共識:即是一個主觀要件。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感情投資問題;一是事后受賄問題。
(一)感情投資問題
逢年過節,有些領導干部收受下級或其他人的“紅包”,雙方在送或收受時并不涉及權錢交易。對此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單位或個人給他人財物,不是因為親友關系互贈禮品,而是因為后者的職位、地位同前者有利害關系,是“用得著的人”,雖然在送財物時沒有提出為自己謀取利益的要求,實際上,是希望以此取得后者的好感,日后需要時可以給予必要的關照。同時,對于接受者而言,其對于送者的意圖也是十分清楚的,雖未明確表示許諾為對方謀取利益,但是雙方“心照不宣”,實際上是“以權力為支點的特殊交易”。因此,對于這種情況應認定為受賄罪。也有觀點認為,即使被告人收受他人財物與本人職務有直接關系,即其職務所具有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能力,是促使他人送財物的基礎,但是按照現行法律規定,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必須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既然雙方在進行財物的收受之時沒有一方利用職務之便為對方謀取利益的約定,認定為受賄罪是于法無據的。還有觀點認為,應具體分析:在排除雙方存在深厚交情的情況下,如果行為人對送禮人的具體請托事項及所送的財物沒有明顯表示反對的,可以認定構成受賄罪;反之,行為人明顯表示反對的,就不能認定構成受賄罪。(1)(P39)
筆者認為,作為受賄罪,“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其主觀要件,這在理論界已達成共識。從罪刑法定角度講,要認定某人構成受賄罪,就必須有證據證明其主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法院紀要》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法院紀要》是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行為要件來看待,最低得有承諾行為,其更為嚴格,目的在于遏制客觀歸罪。在行為人沒有明確的承諾表示時,要認定其收受錢財行為構成受賄罪,就必須能夠證明其明知對方有具體請托事項。這已是一個最低的證明要求。從理論上來講,如果明知對方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他人錢財,這足以表明行為人有為他人謀取利益之目的,根本無須明確的承諾表示。這就是心照不宣。當然,這里的前提是明知對方有具體的請托事項,而不是“對對方所送的錢財沒有明確的反對”。
(二)事后受賄問題
事后受賄,是指事后酬謝型的情況,不是指事先約定先辦事后給錢的情形。對于事后受賄,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受賄故意是指“明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而非法收受賄賂的行為是一種損害其職務行為廉潔性的行為,而故意地實施這種行為。因此在受賄罪中,不僅包括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故意,而且包括為他人謀利益作為非法收受財物的交換條件,即權錢交易的故意。因此,事前沒有賄賂的約定,由于行為人正當行使職務行為在客觀上對他人形成利益,為此受益人在事后向行為人交付財物表示感謝而行為人予以收受的所謂事后受財行為,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雖有收受財物的故意但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交換而收取他人財物的故意,因此不構成受賄罪。”{2} (P629)也有觀點持反對意見,認為刑法理論一般認為,犯罪故意是對犯罪構成要件客觀構成事實的表象和容忍。犯罪構成中的客觀事實包括行為、結果以及因果關系等事實,上述觀點提出權錢交易的故意顯然將權錢交易作為行為來看待,可是在受賄罪中其行為內容并不包括權錢交易,受賄罪中其行為內容并不包括權錢交易,其實行行為只有索取、期約和收受賄賂的部分并無權錢交易。權錢交易是受賄罪的本質,是受賄罪所有行為的濃縮,并非具體行為。此外,事前無賄賂約定的事后受賄,行為人明知是其職務酬勞而予以收受同樣也是權錢交換,唯一不同的是交易順序方面,由此可以認為用權錢交易的故意否定事后受賄的有罪性理由并不充足。{3}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實際上將犯罪故意與犯罪目的混淆了。故意與目的構成罪過的內容,作為故意的認識因素并不包括對目的的認識。作為受賄罪的主觀方面包括受賄故意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兩方面,僅有受賄故意而無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不能構成受賄罪。對于受賄故意的成立,僅需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收受他人錢財違背其職務要求即可。對于“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則意味著行為人收受他人財物是基于為他人謀取利益之目的,或在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前已獲得對方的賄賂許諾。所以,對于事后受賄的情形,雖然行為人有受賄故意,但欠缺“為他人謀取利益”之目的,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是無法成立受賄罪的。
司法實踐中,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兩個問題,筆者認為,立法應該取消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原因有三:(1)受賄罪在形式上表現為權錢交易,但其本質在于侵犯了公職的廉潔性。官員的職責不能與金錢聯系在一起,更不能被金錢所扭曲。作為公職人員,職責就要求其不能非法收受錢財。索賄與非法收賄僅僅是主動與被動的區分,是主觀惡性大小的不同,其本質一樣。所以,非法收賄行為成立受賄罪沒有必要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前提。(2)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給控方帶來證明難度,不利于打擊受賄犯罪。對于收賄者已經為他人謀取了利益,則不難證明。但是,對于受賄者還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情況,要證明其主觀上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則就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賄賂犯罪多表現為一對一的情況,如果受賄人不承認、行賄人不承認,“為他人謀取利益”又沒有外化為客觀行為,如何來認定?如果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就大大減輕了控方的證明責任,可以有力地打擊賄賂犯罪。(3)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還會放縱受賄犯罪分子。比如,對于那些利用職權收受他人賄賂而主觀上并不想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按照刑法規定,就不能構成受賄罪。如此就形成一個怪論:公職人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不(想)給他人辦事,就不構成犯罪;辦事,就構成了犯罪。不管別人的事正當與否。這樣,公職人員只管收錢好了,高枕無憂。規定這一要件,實難以懲處大量的受賄行為。
三、利益正當與否的判斷
對于斡旋受賄罪以及行賄罪,都有一個謀取利益問題。謀取利益正當與否是界定罪與非罪的一個標準。
(一)不正當利益的含義
對于利益正當與否的標準,理論上也曾有過不同的看法:手段不正當說、非法利益說以及違背職務說等。這幾種學說均遭受到批評。最后大家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不確定利益的性質上。不確定利益,是指根據有關法律、政策規定任何人采取合法正當方式、手段或通過正當途徑都有可能取得的利益。這種利益,由其不確定性的特點所決定,對該利益的取得具有競爭性。有人認為,不確定利益不屬于不正當利益,因為利益本體具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其正當與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依賴于人們運用何種手段,通過何種渠道獲得它。也有人認為,對于不確定利益來說,正因為它的不確定性,使得它必須與取得的手段結合起來才有現實意義,離開了手段,它就僅僅只是一個虛無飄渺的、純抽象的概念而已,而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因此,手段對于不確定利益來說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當它與正當手段結合,即采取正當手段取得,就是正當利益;當它與不正當手段結合,’即采取不正當手段,依靠行賄手段排斥競爭對手、損害其他公平競爭者的利益來獲取所謂不確定利益,就是不正當利益。{4}
后一種觀點實質上還是采取手段不正當說,即以手段的正當與否決定利益的性質。利益正當與否是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將手段的正當性與利益的正當性聯系在一起,實際上否定了利益的自身獨立性。目的是正當的,而實現這一正當目的的手段并不一定正當。同理,手段是正當的,但通過這一手段所達到的目的并一定正當。如果通過手段來判斷謀取利益正當與否,那么通過行賄手段謀取的利益就不存在正當的情況。如此以來,立法規定行賄罪的“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一條件就虛置了。當然,持這一觀點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大量的行賄者謀取的都是不確定利益,比如比較典型的買官現象。對此如果不能以行賄罪懲處,可能大家接受不了。但如果按照行賄罪處理,“謀取官職”就必須解釋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然而,要把“謀取官職”解釋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也只能借助于手段的正當與否,單純的“謀取官職”,不能說不正當。畢竟,想升遷也是積極要求進步。正因為如此,大家關于不確定利益的性質的爭論比較激烈,也很矛盾。筆者認為,不確定利益問題的癥結在于立法。在立法上,要限制行賄罪成立的范圍,應該將這一“利益”要件規定為“為謀取非法和不確定利益”。這樣,利益要件就比較好認定了。對于斡旋受賄罪的利益要件,筆者則建議取消。刑法之所以增加這一限制,目的是縮小打擊范圍。但是,這一規定卻不合理。一是有失公平。比如甲為謀取正當利益,找到乙某,給乙送兩萬元錢,乙某利用職權給甲辦了事,則乙某構成受賄罪;假如甲所辦之事不在甲某職權范圍之內,但甲某仍然收下兩萬元錢,而找到丙某把事辦成,這樣甲某就不構成受賄罪。同樣是權錢交易,同樣腐蝕了公職的廉潔性,但結果卻迥然不同。這顯然有失公平。二是容易導致犯罪分子規避法律。如果斡旋人為請托人謀取的是正當利益,那么即使斡旋人索取或者收受錢財都不構成犯罪,這就造成更多人去營造關系網,使得本來可以通過自身職務行為完成的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的行為轉由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來完成,這樣國家工作人員互相利用對方,就都不構成犯罪。
(二)對于司法解釋關于“不正當利益”界定的正確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9年3月4日公布的《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便利條件。”對于這一司法解釋,有人提出了批評,認為其采用了違背職務說,也并沒有超出非法利益說的范疇。并認為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不確定利益既可以采取非法手段、也完全可以采取合法手段,到底采取何種手段,行賄人未必知道、更難以判斷其合法性。用受賄人采取的手段來衡量行賄人利益的正當性,其合理性令人懷疑,甚至可能導致對行賄人的客觀歸罪。{4}也有觀點認為,這一司法解釋注意到手段的重要意義,有其進步性。但認為,所謂利益是行賄人的利益,是相對于行賄人來說的,因此,考察其正當性不應根據受賄人的職務手段來判斷,而應該根據行賄人的手段來判斷。{5}(P231)筆者認為,這兩種批評是沒有正確理解司法解釋含義和精神。對于解釋的第二層含義,其對不正當利益的認定并沒有采取違背職務說或手段不正當性說,仍然是非法利益說。廣義上講,“幫助或方便條件”也是一種利益。司法解釋的第二層含義并不是從受賄者是否違背職務來判斷利益是否正當,而是根據行賄者本人是否在謀取不確定利益的過程中,又謀取了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來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解釋貫徹了立法精神,即限制行賄罪、斡旋受賄罪的成立范圍。
四、“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關系及其認定
“利用職務”是受賄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界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一個標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關系,理論上有很大的爭論,提出了制約關系說、橫向制約關系說、影響關系說以及身份面子說等。制約關系說排除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包括利用他人職務上的便利的情況;橫向制約關系說則把職務之間縱向制約關系納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職務之間的橫向制約關系納入“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之中;影響關系說則把職務之間的制約關系全部納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職務之間的影響關系屬于“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的內容,并認為所謂影響關系主要表現為要求方與被要求方不處于同一職能部門,兩者的職責范圍不具有直接上下級關系,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若不依該國家工作人員要求實行職務行為,對其以后的工作、協作等可能會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這些不利還只是潛在的,不利后果與不依要求實施職務行為之間缺乏必然性。身份面子說更為寬泛,把職務之間的制約、影響關系均納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僅限于利用與職務無關的親屬關系、友情關系和工作關系。2003年《法院紀要》第3條第一項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于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第3條第3項規定,“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如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顯然,《法院紀要》采取了影響說。《法院紀要砂的規定是比較合理的。制約意味著一方的存在和變化以另一方的存在和變化為前提。職務之間存在制約關系,就意味著一方受制于另一方,制約方的意見如果不聽從,會有直接的不利后果。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利用受制方的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和利用自己的職務并無不同。所以,職務之間存在制約關系應劃入“利用職務上便利”的范疇。另外,斡旋受賄畢竟是一種瀆職行為,行為人利用他人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必須與自己的職務有關,否則行為人何職可瀆?所以,對于單純利用親戚朋友關系,就不應納人斡旋受賄內容。職務之間存在影響應該是斡旋受賄的底線。
對于職務之間的隸屬關系,比較好認定,因為這是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一種上下級的關系。領導者基于職務可以直接命令、指使被領導者去實施請托人所請托的事項。問題是,如何理解“職務之間的制約關系”?制約關系首先應該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上下級的關系。制約關系是一種工作上的依存、監督或管理的關系,如果一方不按照另一方的要求來辦理,會有直接的不利后果。當然,這種直接的不利后果并不是必然的,但是否有不利后果的決定權掌握在另一方手里。制約關系包括外部制約關系和內部制約關系:外部制約關系只要有:(1)監督關系。如法院上級之間的監督關系、人大常委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的監督關系、檢察院與相關國家機關之間監督關系等;(2)行業管理關系。行業管理機關與被管理者之間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著被管理者對管理者向自己提出的要求或請求往往是照辦不誤。如稅務、防疫、衛生、工商等部門與所轄區內的相關單位之間就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3)業務制約關系。這主要國有單位與關聯單位之間的業務制約關系。比如國有出版社與承印其圖書的印刷單位之間就存在業務制約關系。如果出版社負責人收受請托人財物,要求印刷單位負責人安排請托人到其單位工作,就應認定出版社負責人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內部制約關系,是指在同一單位內部,組織人事部門、紀檢部門、財務部門與相關部門之間的制約關系。
“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主要是指行為人身居較高的職位、擁有較為廣泛的職權,從而對那些并不隸屬于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產生影響。
“利用一定的工作聯系”,這可分為縱向的工作聯系和橫向的工作聯系。縱向的工作聯系,通常是指上級機關的國家工作人員對其下級機關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職務行為上的聯系。橫向的工作聯系,通常是指在單位內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相互之間有公務關系的不同部門、單位之間,比如公檢法三機關之間,以及這一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與那一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之間,利用職務行為上的影響關系,一方可以憑借自己的職權或地位,左右或者影響另一方,使其利用職權為請托人辦事。
“利用一定的工作聯系”不等同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是指工作自身所提供的便利,同職權本身的行使并沒有必然的直接聯系。實際上,“利用一定的工作聯系”也是利用職務之間的影響關系。
司法實踐中,如何來認定被利用人為請托人謀利是因何種關系呢?筆者認為,這主要從兩方面來認定:職務之間的客觀關系及二人之間的關系。如果職務之間存在隸屬或制約關系,那就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如果職務之間也不存在影響關系,那也排除了“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要查看被利用的人之所以辦事是因職務之間的影響因素還是因二人之間的關系。實踐中,可能存在這幾種情況:一是單純的職務之間的影響因素;二是單純的二人之間的關系;三是既有職務之間的影響因素,也有二人之間的關系因素;四是職務之間的影響因素和利用人的行賄。對于前兩種情況,好處理。對于第三種情況,要分析何種因素起決定作用。例如,某副省長給某部屬高校的校長寫信,要求校長違反國家規定為請托人辦了件事,然后該副省長收了請托人的錢財。對于該案,有人認為被告人雖然身居副省長之職,但他管不著那個大學校長,如果他們之間不認識,他也就不會寫信,因而他只是利用了熟人或者朋友的關系為請托人辦事,其行為與職務沒有關系。也有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屬于利用本人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應構成受賄罪。因為被告人之所以敢于要求大學校長為請托人辦事,主要是因為其身居較高的職位、擁有較為廣泛的職權,從而對那些并不隸屬于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產生影響。筆者認為,對于該案,副省長職位顯然會對大學校長的職務行為產生影響。因為該大學在該省之內,單純從工作出發,該校長也會考慮到學校的工作需要該省支持,副省長的要求還應滿足,否則,會有潛在的不利。當然,盡管二者職務之間存在影響關系,我們還應考察二者的關系。如果二人僅僅就是認識,那么,在該案中,副省長的職務影響因素是主要的;如果二人是同學或朋友,且交往甚密,副省長職務的影響就退為其次了,不能認定副省長是斡旋受賄。所以,當兩種影響都產生影響時,應具體分析哪種因素起決定作用。
對于第四種情況,例如,王某給縣人大常委辦公室主任李某5萬元錢,讓為其違規辦理土地證,李某找到土地局局長,送給局長2萬元把事情辦妥。對于李某的處理,就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李某構成斡旋受賄罪,有人認為李某不構成犯罪,也有人認為李某構成介紹賄賂罪,還有人認為李某構成行賄罪。利用人之所以又行賄,可能是認為自己職務影響不夠,或者認為自己跟對方的關系不夠,或者是出于酬謝對方。對于僅因行賄而促成為請托人謀利的,對行為人按照行賄罪處理;對于職務因素也參與影響的,應按照受賄罪和行賄罪數罪并罰。就李某一案,李某作為人大常委辦公室主任,其職務顯然影響土地局局長的職務行為,應成立受賄罪。因李某又給土地局局長行賄,又構成行賄罪。對此應數罪并罰。
責任編輯:徐岱
【注釋】
作者簡介:單民(1958—),男,河南西平人,法學博士,國家檢察官學院教授;周洪波(1972—),男,河南淮濱人,法學博士,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
*國家檢察官學院,北京 100041
National Prosecutors College,Beijing 100041
[1]《刑法修正案(六)》對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進行了修訂,擴大其主體范圍。從《刑法修正案(六)》的修改來看,該罪應稱為“單位人員受賄罪”。但由于沒有司法解釋對該罪名進行修改,本文仍沿用原罪名。
【參考文獻】{1}參見王俊平,李山河.受賄罪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陳興良.刑法疏議(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
{3}于宏.事后受賄的認定{1}.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3,(1).
{4}鄒志宏.論行賄罪中不正當利益的界定(J).人民檢察,2002,(3).
{5}趙慧,張國忠.貪污賄賂犯罪司法適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