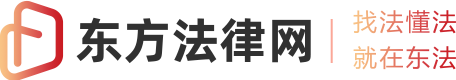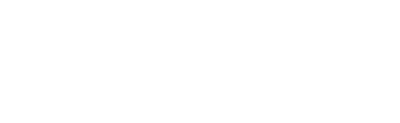優先購買權制度的法律技術分析
- 期刊名稱:《法學》
優先購買權制度的法律技術分析
【關鍵詞】優先購買權 物權效力 債權效力 公示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Technique of the Preemption Right
優先購買權,亦稱為優先承買權、先買權,依通說,其是指權利人依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而享有的于出賣人出賣特定標的物時,得以同等條件優先于第三人而購買的權利。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優先購買權制度并不少見,如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股東優先購買權、合伙人優先購買權等。
但令人遺憾的是,關于我國優先購買權行使的相關規則,各法律規范均規定得十分簡陋,相比較而言,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規則算是較為詳細、完備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法通則意見》)第118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出租房屋,應提前3個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出租人未按此規定出賣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我國《合同法》第230條規定:“出租人出賣租賃房屋的,應當在出賣之前的合理期限內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條件優先購買的權利。”
在實踐中,優先購買權制度運行的實際操作程序和方法仍然存在諸多疑問,產生大量糾紛。即便對于相對規定得較為齊備的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規則,也存在許多質疑和批評,認為相關規則“缺乏邏輯性和現實性”,[1]“明顯不是良法的做法”。[2]在理論上,對于優先購買權制度運行的相關法律技術內涵也仍然缺少真正深入的研究。有鑒于此,以下問題值得澄清與解答:何為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前提條件?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法律后果是什么?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和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的不同法律效力是什么?現實中多發的出賣人未履行通知義務時,優先購買權該如何行使與救濟?該如何保障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的成立?
為回答上述問題,可拋開各類優先購買權制度設立的價值基礎,抽象出各類優先購買權行使的一般規則,合理解釋優先購買權行使各階段的法律內涵,從法律技術角度就優先購買權制度運行中的相關問題給出一個兼顧各方當事人利益的、合乎邏輯的、圓滿的詮釋。
一、優先購買權行使的前提:出賣人與第三人已經訂立買賣合同
所謂優先購買權,即依法定或約定,在出賣人出賣特定標的物時,優先購買權人得在同等條件下優先于第三人而購買該標的物的權利。然具體而言,優先購買權人應當在何時行使該優先購買權,從而使自己在“同等條件下”優先于第三人而獲得該標的物呢?對此,我國現有立法并未明確,理論上也有不同的理解。
第一種觀點認為,優先購買權人在出賣人有出售標的物的意圖時,就應當行使優先購買權。即當出賣人有出售標的物的意圖時,出賣人就應當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如其有購買愿望,當積極和出賣人進行協商,達成買賣合同,出賣人也將只能將標的物優先出售給優先購買權人。以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為例,有觀點認為:“出租人告知的內容,只能是出售出租房屋的意圖……法律規定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立法目的在于提供給承租人一個獲得承租房屋所有權的機會,承租人能否用該機會獲得承租房屋的所有權,有待于在與其他購買人的競買中在同等條件下去實現。”[3]
第二種觀點認為,優先購買權人在出賣人和第三人達成出售標的物的意向時,就應當行使優先購買權。即當第三人和出賣人已經就出售標的物的相關條件談妥,出賣人準備承諾之時,出賣人應當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優先購買權人可以同等條件主張優先購買權。例如,我國有學者認為:“出賣人在與第三人達成合同意向之時,應當再次將擬立合同的有關內容通知優先購買權人。”[4]又如,我國臺灣地區有學者認為:“需等到第三人為一真實的要約,且義務人愿意承諾時,條件即成就,通常義務人會通知權利人此一事實,使權利人于一定期間內行使其先買權。”[5]
第三種觀點認為,優先購買權人應當在出賣人已經和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之后行使優先購買權。即出賣人已經和第三人訂立標的物買賣合同后,出賣人應當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優先購買權人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購買。例如,郭明瑞教授認為:“在優先權存續期間,先買權人未放棄優先購買權的,于出賣義務人與第三人達成出賣標的物的協議時,先買權人得以同等條件購買而主張出賣義務人與第三人的買賣協議無效,由先買權人以‘同等條件’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6]又如,有學者認為:“惟有‘先簽約、后通知’,才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的最典型情形……按照正常做法,華融公司(股權轉讓方)只有在與新奧特集團等(第三方)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后,才能將確定的交易條件告知電子公司(優先購買權人),電子公司也才能據此行使優先購買權。”[7]
對于上述第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其顯然不符合優先購買權的性質和立法目的。優先購買權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證優先購買權人能夠以優惠的條件獲得標的物,從而實現維護社會穩定、保持既有秩序、發揮物之價值等功能。[8]具體方法是,優先購買權人可以不參與和第三人的競買,而只要同意與第三人同等條件,即可以優先于第三人而購得該標的物。由于不參與和第三人的競價,并且在優先購買權人表示愿意購買后,第三人將不得重新報價,這樣的結果必然使優先購買權人將在最終的購買價格上獲得極大的優惠。但是,依第一種觀點,僅僅是在出賣人有出賣意圖時,優先購買權人可以優先和出賣人進行談判,磋商價格,而此時第三人仍可以參與競買,抬高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優先購買權人的優先購買權還有什么價值呢?其和普通買賣合同的訂立又有什么區別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對于上述第二種觀點,筆者認為,其可能也難以實現優先購買權制度的立法目的,難以充分保護優先購買權人的利益,且理論上也難以自圓其說。這種觀點和第一種觀點相比,顯然是有進步的,其要求“出賣人在與第三人達成合同意向時”,或“第三人為一真實的要約,且義務人愿意承諾時”,出賣人應當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并使優先購買權人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購買。此時第三人愿意購買標的物的條件已經相對確定,優先購買權人已經無需再和出賣人或第三人就買賣條件進行談判或競價,若能夠以此價格購買到該標的物,對于優先購買權人而言仍然是十分優惠的。但問題是,這樣一些“合同意向”、“真實要約、愿意承諾”,有多少確定性、可操作性?又有多少法律強制力呢?如在優先購買權人表示愿意購買的情況下,出賣人或第三人又違反了“合同意向”或“承諾意愿”,或不愿出售標的物,或抬高價格,此時,優先購買權人又該如何行使權利呢?是否出賣人或第三人不得違反該“合同意向”或“承諾意愿”,而必須將標的物以確定條件出售給優先購買權人?其法律依據何在?鑒于上述諸多難點,筆者認為,在出賣人和第三人僅僅達成出售標的物的意向時,優先購買權人仍然不具備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條件。
對于上述第三種觀點,筆者認為其是正確的,是符合優先購買權制度價值的,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和邏輯性。一方面,在出賣人和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的情況下,出賣該標的物的同等條件必將確定。此時,優先購買權人可以直接據此主張優先購買權,購得該標的物,從而免除了再與出賣人或第三人競價的煩惱,必然使購買條件大為優惠。另一方面,在出賣人已經和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的情況下,相關出售情況已經固定且明確,此時,出賣人或第三人也無法再否認或推翻相關事實,不像所謂的“合同意愿”、“承諾意愿”等缺少相應的法律約束力,從而保證了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可操作性和便宜性。
優先購買權的行使以出賣人和第三人已經訂立買賣合同為前提,這種觀點雖然未得到我國民法學界的廣泛贊同,但筆者認為,它是符合傳統民法中對于優先購買權制度的基本理解的,并且有相關理論、立法和實務予以支持。德國學者鮑爾教授和施蒂爾納教授認為:“先買權行使之前提條件,為出賣人與第三人之間已達成有效之買賣契約。”[9]《德國民法典》第463條規定:“就某一標的物而言有優先買受的權利的人,一經義務人和第三人訂立關于該標的物的買賣合同,即可以行使先買權。”第469條第1款規定:“義務人必須將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的內容不遲延地通知先買權人。”《瑞士民法典》第681條a項規定:“出賣人須將買賣契約的締結及內容告知先買權人。先買權人欲行使先買權的,須在知悉契約的締結和內容之日起的三個月內行使該權利。”我國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995年第五次民庭總會決議:“‘土地法’第104條所指優先購買權,是否需以所有人與第三人間有買賣土地或房屋契約之存在為要件?……此形成權之行使,須以行使時所有人與第三人間有買賣契約之存在為要件。”
理論上,也有學者對于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應當以出賣人和第三人已經訂立買賣合同為前提提出了質疑,即無法理解在已經存在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的情況下,如何承認并保護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后所產生的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的買賣關系。那么,究竟應當怎樣解釋并協調這兩個買賣關系的效力呢?對此,下文將予以分析。
二、優先購買權行使的后果: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的雙重買賣關系
雖然對于優先購買權的性質存在爭議,但通說認為,優先購買權應當是一種形成權,隨著優先購買權人的單方意思表示即成立其和出賣人之間的買賣關系。[10]
既然優先購買權是一種形成權,在出賣人和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的前提下,隨著優先購買權人的單方意思表示,其就成立了和出賣人之間的買賣關系,而無需征得出賣人同意,更不用說第三人的意愿了。在此情況下,既然不需要出賣人或第三人為任何行為或意思表示,那么,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的效力應當說并沒有受到影響,而應當是繼續存在并有效的。由此產生的問題是,一方面,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買賣關系都是合法存在的,而另一方面,出賣的標的物是特定的、唯一的,那么,此時應當如何協調這兩個買賣關系之間的效力呢?
筆者認為,既然沒有理由認為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因為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成立優先購買權人和出賣人之間的買賣關系而受到影響,那么,此時就應當承認這兩個買賣關系均是有效的,即形成了一物二賣的雙重買賣關系。
雖然國內學者對此鮮有論及,但實際上,此時兩個買賣關系的效力屬于雙重買賣,也為傳統民法所一向認同。例如,德國學者曼弗雷德·沃爾夫教授認為:“權利人(指先買權人)通過單方面的形成表示和他(指義務人)簽訂買賣合同。因此,對義務人而言就存在同一物的兩個買賣合同:一個是與第三人簽訂的愿意出賣標的物的合同,一個是權利人通過單方面的形成表示產生的買賣合同。”[11]又如,王澤鑒教授認為:“所應注意者,是出賣人與第三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性質,并不因優先承買權之行使而受影響。出賣人對于優先承買權人及第三人均負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義務。出賣人欲對優先承買權人履行,并避免第三人主張損害賠償時,必須與該第三人約定,僅在優先承買權不行使之場合,始負履行義務。反之,出賣人對第三人為履行時,違反其對優先承買人之義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2]
對于此時成立雙重買賣關系,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了異議:“先買權人依此標準行使先買權的結果,將在出賣人與第三人之間、出賣人與先買權人之間分別成立兩個內容完全相同的合同,出賣人由此被迫陷入二重買賣的尷尬境地。”[13]為了避免上述“尷尬境地”的出現,這位學者還設計了其他的思路,試圖回避這種雙重買賣現象的出現。但令人遺憾的是,其設計思路的結果是,“在此二種情形,先買權人與出賣人所達成的買賣僅為通常的買賣,并非行使先買權的結果。”[14]
筆者認為,實際上,在形成雙重買賣之后,并不會出現什么履行上的麻煩或“尷尬境地”。此時,出賣人和第三人、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的買賣關系均是合法有效的,出賣人均負有履行義務。但是,標的物是唯一的,只能有一個買賣關系得到實際履行。具體向誰履行,因為出賣人還是標的物的所有權人,故其應當享有決定權。出賣人履行了標的物交付義務的買賣關系將因此而消滅,而另一個未得到履行的買賣關系,將應由出賣人對其承擔履行不能的賠償責任。具體而言,如上述王澤鑒教授所言:“出賣人欲對優先承買權人履行”,必須與第三人約定有一定免責條件,否則將向第三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出賣人對第三人為履行時,違反其對優先承買人之義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由此可知,在承認雙重買賣的情況下,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兩個買賣合同的效力以及履行均不存在法律上的阻礙。在承認買賣關系效力的前提下,任何一個未能得到實際履行的當事人,均可以通過損害賠償的方式得到救濟,以實現利益平衡。總之,筆者認為,引入雙重買賣概念來界定此時出賣人和第三人、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的兩個買賣關系是非常合理和周延的。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優先購買權人和第三人均有權要求出賣人向自己為標的物的交付,但是在雙重買賣的情況下,這將完全取決于出賣人的意愿。在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情況下,出賣人向第三人為交付時,優先購買權人將只能轉而要求出賣人為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但是,在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情況下,依通說,該優先購買權具有物權效力,是可以對抗第三人的。那么,此時出賣人向第三人所為的交付與優先購買權人權利的物權效力之間的關系又如何協調呢?下文將對此予以分析。
三、優先購買權的法律效力: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和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之差異
在論及優先購買權時,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是,優先購買權分為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和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依通說,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僅僅具有債權效力,只能在優先購買權人和出賣人之間主張,不能對抗第三人;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則具有物權效力,不僅可以在優先購買權人和出賣人之間主張,還針對第三人發生法律效力,可以對抗第三人。[15]
需要說明的是,不論是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還是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優先購買權人均只能在出賣人已經和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的前提下方才可以行使優先購買權,且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后將形成雙重買賣關系。依優先購買權,優先購買權人有權要求出賣人首先向自己為標的物交付,相應地,出賣人也負有優先向優先購買權人為履行的義務。只不過若是出賣人不履行此項向優先購買權人首先履行的義務時,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和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將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若是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該優先購買權僅僅在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發生效力,優先購買權人僅僅對于出賣人可以要求其優先向自己為買賣關系的履行,而不得以此權利對抗第三人。換言之,若出賣人向第三人首先為了履行,優先購買權人將無能為力,只能轉而要求出賣人承擔相應的債務不履行的責任。正如迪特爾·梅迪庫斯教授所言:“行使先買權僅使權利人取得移轉受先買權拘束的標的物的債權。在此種情形,義務人(出賣人)只能通過將標的物讓與第三買受人或者讓與一個第四人來破壞履行。在這種情況下,權利人(優先購買權人)通常被限定在指向義務人(出賣人)的替代給付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上。”[16]
若是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優先購買權人的此項權利的效力不僅僅及于出賣人,即其不僅僅可以要求出賣人首先向自己為標的物的交付,還可以對抗第三人,換言之,若出賣人向第三人首先為了履行,出賣人的此項履行行為有違于優先購買權人的權利,則將被宣告無效。依照德國法的理解,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將獲得“預告登記”的法律效果,任何與該優先購買權(預告登記)的內容相沖突的物權變動都將被宣告無效。例如,鮑爾教授和施蒂爾納教授認為:“物權性的先買權所追求的亦是這一目的:……,在發生先買權事由后,對第三人來說,先買權人之法律地位,與通過預告登記而被保護者之法律地位相同(民法典第1098條第2款)。”[17]又如,曼弗雷德·沃爾夫教授認為:“物權性質的先買權可以為他提供擔保。由于先買權具有與預告登記相同的效力,它保證使違反先買權的處分相對無效(第1098條第2款、第883條第2款),權利人可以要求第三人同意在土地登記簿中登記為所有權人(第1098條第2款、第888條)。”[18]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出賣人仍然可以向第三人首先為標的物的交付,但是,由于這種交付是有違于優先購買權人的優先購買權內容的,將產生類似于與預告登記內容相沖突的法律后果,即該履行對于優先購買權人而言是“無效的”,優先購買權人可以依據自己的優先購買權而要求第三人“同意在土地登記簿中將自己變更登記為所有權人”。如此情況下,出賣人是無法向第三人首先為實際交付的,即便首先交付,也是沒有效力的,而優先購買權人可以依據其和出賣人之間的買賣關系要求后者向自己為實際交付,并因此獲得標的物的所有權。
由于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所具有的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出賣人和第三人此前所簽訂的買賣合同將可能會形同虛設,得不到實際履行,并可能產生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問題。就出賣人而言,因為其將無法向第三人為標的物的實際交付,故而應當承擔相應的債務不履行賠償責任;就第三人而言,因為其將無法獲得出賣人的實際交付,故而將是白費相關的談判成本,并可能還要面對難以向出賣人追討已經履行的對待給付的風險。
可喜的是,對于這一承認優先購買權物權效力的后續問題,傳統民法也是有相關配套措施的,從而保護出賣人和第三人的利益:(1)就出賣人的保護而言,一方面,為了避免出現不能向第三人為交付時的賠償責任,“出賣人可考慮在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中約定該合同的履行以先買權人不行使先買權為條件,或者約定在先買權行使的情況下,出賣人保留對該合同的解除權。”[19]如此,出賣人可以通過附加合同解除權的形式消滅其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并進而免除交付不能的損害賠償責任。另一方面,由于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一般均是公示公知的,故第三人明知存在該風險而仍然與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也可以據此認為其自愿承擔相關風險,并因此免除出賣人履行不能的賠償責任。正如鮑爾教授和施蒂爾納教授所言:“但出賣人對于買受人(第三人)所承擔的責任(因違反使買受人取得權利之義務),依據民法典第439條(買受人知悉權利瑕疵)之規定,通常并不成立。”[20](2)就第三人的保護而言,一方面,如下文將要詳細論述的一樣,所有的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都應當是公示公知的,因而,第三人在明知存在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放棄和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如果其自愿承擔風險而訂立了買賣合同,那么,由此引起的標的物不能實際交付的風險,以及談判成本的浪費,也就只能是咎由自取,自行承擔了。另一方面,為了保證第三人在不能實際得到標的物交付的情況下能夠順利地實現對出賣人已進行的對待給付的追討,德國法上還賦予了第三人留置已經實際得到的標的物,以確保出賣人歸還已進行的對待給付的權利。如曼弗雷德·沃爾夫教授所言:“第三人作為買受人享有第1100條的留置權,直到出賣人,也就是先買權義務人,返還第三人支付的價金為止。”[21]
四、優先購買權的非常態行使:出賣人未履行通知義務時。優先購買權的行使和救濟
如前所述,優先購買權行使的正常程序應當是:(1)優先購買權人基于法定或約定,對于某特定標的物享有優先購買權。(2)出賣人和第三人訂立標的物買賣合同。(3)在出賣人將其和第三人訂立的標的物買賣合同的具體內容通知優先購買權人的情況下,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憑著單方面的意思表示,從而成立優先購買權人和出賣人之間的買賣關系。(4)存在出賣人和第三人、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的雙重買賣關系,第三人和優先購買權人均有權要求出賣人履行買賣關系,交付標的物。(5)若是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該優先購買權僅在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之間發生效力,若出賣人向第三人為了標的物交付,優先購買權人將只能向出賣人追究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責任。(6)若是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該優先購買權可以對抗第三人,產生類似于預告登記的效果,若出賣人向第三人為了標的物交付,該交付將是無效的,優先購買權人有權要求予以撤銷,并向自己為標的物交付。此時,第三人將只能要求出賣人承擔相應的債務不履行的賠償責任。
上文已分析了優先購買權正常行使情況下各階段的法律關系和法律效果,但在實踐中,引起大量糾紛的情況是:出賣人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并辦理了標的物交付手續,而此間卻一直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直至優先購買權人發現自己享有優先購買權的標的物已經出讓給了第三人,并由此發生糾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怎樣保護優先購買權人的利益呢?其應當享有什么樣的權利呢?該權利又是什么性質呢?
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國內學術界的多數看法是,此時優先購買權人的優先購買權受到了侵犯,因此,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這一侵害優先購買權人利益的合同的效力是有瑕疵的。以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為例,具體有兩種理解:(1)優先購買權人可以宣告該合同無效。其依據是,《民法通則意見》第118條規定,承租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宣告該房屋買賣無效。(2)優先購買權人可以申請撤銷該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楊巧麗訴中州泵業公司優先購買權侵權糾紛案”典型案例中,當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就是“請求判令撤銷被告的房屋出賣行為”。[22]
將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定位為無效或可撤銷合同的最大問題在于:如前所述,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前提是存在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而現在該買賣合同被宣告無效或撤銷了,那么,優先購買權人又該依據什么行使自己的優先購買權呢?如果不能行使自己的優先購買權,優先購買權人將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宣告無效或撤銷,又有什么意義呢?難道只是為了發泄一下自己心中的怒氣,干一件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嗎?正如我國臺灣地區1980年臺上字二九五三判決所言:“‘土地法’第34條之一規定之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以共有人與買受人間之買賣存在為前提,如該買賣被撤銷而不存在,即無優先承購權可言。”對此,我國學者亦有同感:“在買賣合同被宣告無效后,據此確定的‘同等條件’即應隨之失去效力,由此導致承租人無法再以‘同等條件’行使優先購買權。”[23]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對于出賣人一直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其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內容而直至優先購買權人自行發現從而發生的糾紛,并不應當理解為是對優先購買權人優先購買權的侵害,并進而試圖消滅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的效力。實際上,此時,優先購買權人的優先購買權仍然存在,并且在其獲知出賣人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相關內容后,即可以行使優先購買權,成立其和出賣人之間的買賣關系,并進而出現雙重買賣的后果。其具體法律效果,如同前文所述的優先購買權正常行使后的法律效果。唯一區別在于,通常應當是出賣人主動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其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內容,而現在是優先購買權人通過其他途徑自行獲知該買賣合同內容。
實際上,上述觀點也得到了許多學者和判例的支持。例如我國臺灣地區1958年臺上一五一判例所言:“故承租人如未接獲出賣條件之書面通知,仍非不得請求確認其就耕地有優先承買權之存在。”又如,戴孟勇先生認為:“反之,如果不賦予承租人請求法院宣告出租人與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無效的權利,而是允許承租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并規定出租人與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對承租人不發生效力,那么優先購買權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可實現,第三人也可通過追究出賣人的違約責任而使其利益得到保障。”[24]
還需要研究的是,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應當有期限的限制。在出賣人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其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相關內容的情況下,優先購買權人自然可以行使優先購買權。但是,該權利的行使期限也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我國臺灣地區立法多限制為收到通知后的10天或15天。[25]我國《民法通則意見》以及《合同法》所規定的應提前“三個月”或在“合理期限”內通知優先購買權人,顯然缺少可操作性,已經受到了各方學者的普遍質疑。[26]那么,在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其和第三人之間買賣合同相關內容,而由優先購買權人自行獲知相關內容時,其行使優先購買權有沒有時間的限制呢?
筆者認為,為了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也應當對于優先購買權人自行獲知相關買賣合同內容時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期限做出一定的限制。如有學者建議:“如果出賣人未通知先買權人,先買權人須在知悉出賣人和第三人締約之日起3個月內行使先買權,但先買權自出賣人與第三人締約之日起1年內不行使而消滅。”[27]在筆者看來,這個期限規定有一定合理之處,值得借鑒。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上述期限內,優先購買權人知悉相關買賣合同內容,自然可以行使優先購買權。但是,若是在上述期限以外,優先購買權人方才知悉相關買賣合同內容,因期限經過,優先購買權消滅,優先購買權人將不能再行使優先購買權,要求出賣人為標的物的交付,但是,仍然可以追究出賣人未為通知而侵害其優先購買權的責任。正如王澤鑒教授所言:“出租人出賣土地,未經通知承租人即移轉土地所有權于買受人者……,是違反通知義務,侵害形成權,致其不能行使,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8]
五、優先購買權與第三人利益保護:公示與優先購買權的物權效力
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的性質決定了其應當通過一定的方式予以公示,從而保護第三人的利益。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能夠對抗第三人,將可能使出賣人和第三人所訂立的買賣合同的效力完全落空,此將可能給第三人造成巨大的損失。因為合同的訂立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當事人艱苦地討價還價,凝聚了大量的無形勞動,花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如果因為優先購買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而使好不容易訂立的合同消滅掉,顯然對于第三人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因此,筆者認為,應當通過一定的公示程序使第三人能夠在與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之前就知曉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的存在,從而使其能夠預先評估其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的風險。
對于約定優先購買權,如果要想取得物權效力,一般認為,均需要進行登記、公示。如孫憲忠教授所言,在德國,“物權先買權的設立,首先需要當事人即先買權取得人和不動產出賣人達成合意,然后就權利的設立進行登記。物權先買權同樣在登記時成立。”[29]換言之,如果優先購買權人希望自己和第三人約定的優先購買權能夠取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那么,除了和第三人之間就該優先購買權的相關內容達成協議外,還必須像設立不動產物權一樣,在不動產登記簿進行登記。一旦進行了這一優先購買權登記,優先購買權人將會取得預告登記的效果,取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對于法定優先購買權,有觀點認為,因為其是法律明定的優先購買權,故其當然地具有物權效力,而無需進行公示。例如,法律“僅規定先買權,而未明文規定其物權的效力者,解釋上亦應予以物權的效力”;[30]“有學者認為法定優先權具有物權效力,蓋以為法定先買權,無須為預告登記,權利本身已具有預告登記之效力。”[31]
對于上述觀點,筆者不能贊同,即便是法定優先購買權也好,如果要取得物權效力,同樣應當予以一定方式的公示。一項優先購買權是否應當賦予物權效力,這是由立法機關根據社會經濟條件而決定的,無可厚非。但是,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將因此否定此前出賣人和第三人所訂立的買賣關系,第三人花費無數人力、財力,寄予無限希望的買賣合同將因此落空。因此,我們應當設計適當的法律制度,保證第三人在與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之前就知曉這一風險的存在,使其有足夠的空間評估自己與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的風險,并做出抉擇,或采取一定的規避措施。這一適當的法律制度就應當是公示制度。
筆者的這一觀點也可在許多學者那里得到贊同。如戴孟勇先生認為:“無論法定先買權還是約定先買權,只要已采取了法律規定的適當方式予以公示的,即應確認其具有物權性效力,可以對抗第三人,如未采取適當的方式公示,則應僅具有債權的效力,其行使即不得對抗第三人。”[32]王澤鑒教授也不贊同前述楊與齡教授的觀點,[33]其主要理由在于:“優先承買權之物權性對第三人之影響甚巨,必須有公示之表征方法,依‘現行法’規定,房屋及基地之租用,不必登記,第三人無由知之,難免遭受不測之損害。……,承租人為保護自己的權利,得為預告登記。”[34]
在實踐中,筆者發現,各立法例在賦予優先購買權以物權效力的同時,其實也都是配套以公示制度的。在沒有公示時,往往只有債權效力,而具有物權效力時,往往必須輔之以公示制度。此點在我國臺灣地區有關基地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國臺灣地區原“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出租人出賣基地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人有依同樣條件承買之權。”租賃關系是不需要登記公示的。因此,在當時,此項優先購買權僅僅具有債權效力。[35]1975年,我國臺灣地區“土地法”第104條修改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據此規定,此時的基地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取得了物權效力,是可以對抗第三人的。相應地,該“土地法”同時規定了第102條:“租用基地建筑房屋,應由出租人與承租人于契約訂立后2個月內,聲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地上權之登記。”使用他人土地,登記為地上權,自然比租賃關系更為穩妥,因此,可以預見,基地承租人肯定是愿意對自己的基地租賃關系進行地上權登記的。此時,仍依據租賃關系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情形,顯然將會大為下降。而地上權一經登記,不就取得公示效果了嗎?既然已經登記公示,自然可以提醒第三人不要不慎侵害他人的優先購買權。為了嚴格貫徹登記公示制度,保護第三人利益,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還特別強調:“享有該條的優先購買權,地上權、典權應當經過登記,未經登記的地上權、典權人,不享有此優先權。”[36]
在我國,許多優先購買權的存在價值受到質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該優先購買權事先并未公示,并不為第三人所知悉,而在第三人已經和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之后,優先購買權人則出面主張優先購買權,如此,對于第三人顯然是不公平的。以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為例,其為法定的優先購買權,且依《民法通則意見》,優先購買權人可以宣告出賣人和第三人之問的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即具有物權效力。在實踐中,很多情況是,第三人是在不知該房屋已經出租的情況下和出賣人訂立了買賣合同,而此后,承租人主張優先購買權。在我國實踐中租賃是不登記的,因此第三人完全無法知悉該租賃關系的存在,而此后由于承租人法定的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的存在,該買賣合同將完全落空,這顯然對于第三人是完全不公正的。但實際上,我國法律在規定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同時,其實是要求房屋租賃予以登記備案的。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53條、《城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第13條均規定房屋租賃合同應當向房產管理部門登記備案。但是,根據我國《合同法》第44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9條規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手續,或者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才生效”,而未辦理批準、登記手續的合同方才無效。《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僅僅是要求房屋租賃關系備案,而非登記生效。因此,若當事人未進行登記備案,該房屋租賃合同仍然應當是有效的,承租人仍然應當享有優先購買權,且是物權效力的,而第三人則完全可能對于該租賃事實卻一無所知。如此的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的實際運行狀況遭受到廣泛的質疑和批評,恐也就不難理解了。也許正是看到了租賃關系不公示和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物權效力之間的不銜接,為了保護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處理房屋租賃糾紛若干法律適用問題的解答(二)》(2005年8月29日公布)做出了如下規定:“租賃合同中的承租方依照法律規定依法享有優先購買權,不因登記與否而影響該項權利。但是,未經登記的租賃合同,其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不得對抗第三人。”照此理解,如果租賃合同沒有登記備案,承租人還是有優先購買權的,但僅僅是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是不能夠對抗第三人的,即沒有物權效力。筆者認為,這種理解和變通是符合法理的,有效地解決了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物權效力和租賃關系不公開之間的矛盾,公平合理地兼顧了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
還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保護第三人利益,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必須予以公示,但是,該公示僅僅需要公示產生優先購買權的基礎法律關系即可,而無需公示優先購買權的存在。以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為例,僅僅需要在房屋所有權證上登記存在租賃關系即可,而無需登記存在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以股東優先購買權為例,僅僅需要在工商登記中記載存在若干其他股東即可,而無需登記存在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如學者所言:“因法定先買權僅存于法律規定的幾種法律關系中,故其公示方式只須將產生先買權的基本法律關系予以登記即可。”[37]究其原因在于,法律上認為,“法定的權利是公知的”,只要法律上有明確規定的權利,即應當認為相關當事人均知曉此項權利的存在,并應當遵照此項權利予以執行,而無需單獨再就此項權利通知相關的義務人。否則的話,任何法律的執行都以相關義務人知曉此項法律的存在為前提,而法律又是無法保證確實為人人所周知的,更何況即便當事人知曉,其也可以不知而推托,那么,法律在現實社會中將因此寸步難行,無法真正實施。據此,筆者認為,法律規定的權利即應當認為相關當事人是知曉,并應當遵守的,正所謂“任何人都不得推托不知國法”。[38]基于以上認識,既然各類法定優先購買權的存在是法律所明定的,是相關當事人所明知的,那么,只要公示法定優先購買權的相關基礎關系就應當可以了,而無需再就所謂的各種優先購買權進行公示。如公示存在租賃關系,就應當知道存在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如公示存在參股關系,就應當知道存在股東優先購買權;如公示存在合伙關系,就應當知道存在合伙人優先購買權。此點也得到了學者的認可,如在北京新奧特集團等訴華融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有學者認為:“公司享有股東優先購買權是法定權利,凡欲購買公司股權的第三人,均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存在優先購買權,即使華融公司未再行通知或者告知優先購買權的存在。”[39]實際上,最高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也是支持這種觀點的:“華融公司(出賣人)和新奧特集團(第三人)在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時,均知悉公司法規定的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40]
最后,還需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筆者認為,雖然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公示的主要方式是登記,但也不排斥其他的使第三人所公知的公示方式。一般而言,最常見的公示方式是登記,如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需將租賃關系記載于房屋所有權簿中,股東優先購買權需將股權份額記載于工商登記中。但是,也不排斥其他的公示方式也能使優先購買權產生物權效力,其主要體現在共有人的優先購買權中。若是不動產共有人的優先購買權,因為不動產均需要登記,其共有人的地位也因為登記簿的載明而予以了公示,此不存在任何問題。但若是動產共有人,依據《民法通則》第78條、《物權法》第101條,在其他共有人出讓共有份額時,仍然享有優先購買權。此時,該動產共有關系是不進行登記的,但是,若其他共有人是以共有人的名義轉讓共有物份額的,則第三人就應當知曉有其他共有人的存在。如此,該動產共有關系將因為共有人的承認而為第三人所知曉,則此時,應當同樣認為該共有關系取得了公示的效果,相應地,也應當可以賦予動產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以物權效力,取得對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當然,若共有人謊稱動產為其一人所有,而善意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其發生交易,第三人將獲得該動產所有權,但此時應屬于善意取得的后果,已經不是優先購買權的問題了。
【注釋】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法學院。
[1]許尚豪、單明:《優先購買權制度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頁。
[2]楊會:《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制度之反思》,栽易繼明主編:《私法》(總第1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頁。
[3]魏秀玲:《出租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法律問題之探討》,《政法論壇》2003年第3期。
[4]同前注[1],許尚豪、單明書,第185頁。
[5]謝哲勝、張靜怡、林學晴:《選擇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5頁。
[6]郭明瑞:《論優先購買權》,《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5年第5期。
[7]葉林等:《股權優先購買權對股權轉讓效力的影響——北京新奧特集團等訴華融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糾紛案》,王利明主編:《判解研究》(總第29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8]參見劉文娟:《優先購買權的法律性質及其制度價值》,《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
[9](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10]參見王澤鑒:《優先承買權之法律性質》,載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頁;(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等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頁。
[11](德)曼弗雷德·沃爾夫:《德國物權法》,吳越、李大雪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頁。
[12]同前注;[10],王澤鑒書,第508頁。
[13]戴孟勇:《先買權的若干理論問題》,《清華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14]兩種設計為:“可考慮確立一定的規則,以便在出賣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之前即確定先買權人是否愿意購買。具體言之:其一,如買賣條件系賣方自定,則賣方可以此通知先買權人是否購買。如其不愿購買。嗣后在第三人以該條件或高于該條件而與出賣人訂立合同時,即不得再主張先買權。如賣方因無人應買而降低條件時,仍應通知先買權人,以確定其是否購買。其二,如買賣條件系由第三人提出,出賣人在準備承諾之前應將該條件及意欲承諾之意思通知先買權人,以確知其是否愿買。一旦先買權人決定購買,應立即通知出賣人,嗣后出賣人不得以他人有更優條件為由予以拒絕。如此區分之目的,乃在于盡早確定先買權人的購買意愿,以避免二重買賣的發生。”同上注。
[15]同前注[9],鮑爾/施蒂爾納書,第464頁;同前注[5],謝哲勝、張靜怡、林學晴書,第70頁;陳銘福:《土地法導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69頁。
[16]同前注[10],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132頁。
[17]同前注[9],鮑爾/施蒂爾納書,第464頁。
[18]同前注[11],曼弗雷德·沃爾夫書,第243頁。
[19]同前注[13],戴孟勇文;同前注[10],王澤鑒書,第508頁。
[20]同前注[9],鮑爾/施蒂爾納書,第468頁。《德國民法典》第442條(在2002年債法修改前原為第439條)規定:“買受人在訂立買賣合同時知道瑕疵的,因瑕疵而產生的買受人的權利即被排除……”
[21]同前注[11],曼弗雷德·沃爾夫書,第244頁。
[22]參見“楊巧麗訴中州泵業公司優先購買權侵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4年第5期。
[23]戴孟勇:《房屋整體出售與部分房屋承租人的優先購買權》,王利明主編:《判解研究》(總第25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頁。
[24]同上注,戴孟勇文。
[25]參見我國臺灣地區“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土地法”第104務、“民法”第426—2條之規定。
[26]參見張曉梅:《是否繼續保護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法律適用》2003年第5期;鐘濤:《房屋承租人優先購買權若干爭議之解決》,《法律適用》2005年第10期;王朝輝:《出租人先買權的法理性質及其糾紛處理》,《法律適用》2003年第9期。
[27]夏志澤:《先買權新論》,《當代法學》2007年第2期。
[28]同前注[10],王澤鑒書,第510頁。
[29]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頁。
[30]鄭玉波:《論先買權》,《法令月刊》第25卷第12期。
[31]楊與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實用》,第140頁。轉引自前注[10],王澤鑒書,第508頁。
[32]同前注[13],戴孟勇文。
[33]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王澤鑒教授的《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中,原文為“依余所見,仍以其見解為是……”,即意味著王澤鑒教授是贊同楊與齡教授觀點的。但是,在臺灣大學法學叢書1998年版的王澤鑒教授的《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臺灣原版)中,原文為“依余所見,仍以‘最高法院’見解為是……”,即意味著王澤鑒教授是不贊同楊與齡教授觀點的,而是支持相反的我國臺灣地區“最高法院”的觀點。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字及觀點,考慮到版本的權威性,顯然還是應當以臺灣原版文字及觀點為準。
[34] 同前注[10],王澤鑒書,第508頁。
[35]如我國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970年臺上字第2264號判決所言:“‘土地法’第104條之優先承買權……僅為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權利義務,并無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僅得請求其承租人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失,不得主張第三人承買房屋為無效。”
[36]陳銘福:《白話六法——土地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38頁。
[37]李敬從:《論先買權若干問題》,《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
[38]《法國民法典》,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譯者注。
[39]同前注[7],葉林等文。
[40]同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