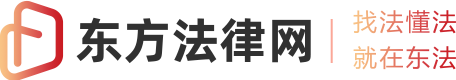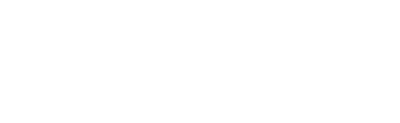集資詐騙罪與傳銷犯罪的區別
- 期刊名稱:《人民司法(應用)》
一、傳銷犯罪行為人希望通過傳銷組織牟利,而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集資款為目的,二者的主觀目的存在明顯差異。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下簡稱傳銷犯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構成集資詐騙罪。相比較來看,傳銷是一種非法的經營手段,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罪名之前,對于此種行為一直定性為非法經營罪,其主要侵犯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集資詐騙行為人實施的是非法集資行為,其主要侵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依法懲處非法集資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非法集資的主要特征有:一是未經有關監管部門依法批準,違規向社會(尤其是向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二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出資人貨幣、實務、股權等形式的投資回報;三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集資目的。由于傳銷組織往往發展迅速,能在短期內聚集大量的人員和款項,很多集資詐騙行為人往往采用傳銷式的組織形式來進行集資詐騙活動。正是由于這種“披著傳銷外衣的集資詐騙”情況的存在,導致對兩罪的認定極易產生混淆,特別是容易將傳銷犯罪通通誤認為是集資詐騙罪,產生種種誤解,例如,只要有欺騙行為就是集資詐騙、傳銷組織最頂層的發起者構成集資詐騙、傳銷項目的都是集資詐騙等誤區。事實上,即便集資詐騙行為人采用類似傳銷的方式,其與傳銷犯罪也存在一些本質上的區別,應將二者進行明確區分,以便正確定罪量刑。
(一)首先,要理解二罪之間主觀目的的差異性,必須先摒除一個錯誤的觀念:只有詐騙犯罪才具有欺騙性。集資詐騙罪與詐騙罪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集資詐騙罪同樣具有詐騙罪的重要特征—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為目的。也就是說,行為人的目的是直接侵害他人財產,將財產作為犯罪的對象。關于集資詐騙行為具有欺騙性,這毋庸置疑。也正因如此,極易產生一個誤區:只要用欺騙方法吸收投資人資金,就是集資詐騙罪。這種觀念是十分錯誤的:傳銷犯罪與集資詐騙犯罪均具有欺騙性,不能僅憑此來區分兩罪。事實上,并不是只有詐騙犯罪才具有欺騙性。行為具有欺騙性的犯罪還有虛假廣告罪、串通招投標罪等等。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傳銷是“……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可見,傳銷犯罪本身也具有欺騙性,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正是通過騙取參加者加人組織,以傳銷這種非法的組織形式來謀取利益的。可以說,騙取財物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傳銷活動的基本特征或者構成要件要素。[1]對于這一點,法律有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達成共識:在傳銷活動中,為了不斷發展人員加人,行為人通常用高額利潤作誘餌,夸大或虛構傭金或獎金收人,收取高額入門費或強制購買產品,這似乎具有某些詐騙罪的特征,但傳銷中參加者是追逐高額回報而加入其中的,其決定交易是受到利益的誘惑,而不是因虛構事實、行為誤導而產生的錯誤認識,故其行為不是受害者行為,不受法律保護。[2]可見,并不是只要通過欺騙方法吸引投資人投資,就構成集資詐騙犯罪,該行為同樣可以構成傳銷犯罪。
(二)傳銷犯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通過資格、層級等銷售模式謀取非法利益,而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騙取、非法占有他人財物。雖然集資詐騙罪與傳銷罪都具有欺騙性,但二者的“騙”是有區別的。傳銷罪是從直銷而來,直銷是一種銷售方式,即直銷企業招募直銷員,繞過傳統批發商或零售渠道,直接向最終消費者進行銷售。這種銷售方式在我國是必須經過批準的。而傳銷往往是披著直銷的外衣來吸引參加者以騙取財物。國務院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指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人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由此可見,傳銷是通過資格、層級、人員數量這種銷售模式牟取非法利益的行為,為國家所禁止。
由于刑法在傳銷罪的罪狀描述中使用了騙取財物一詞,致使司法實踐中往往將傳銷罪中騙取財物與集資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相混同。也就是說,將集資詐騙的“騙”,與傳銷罪中的“騙”相混同。為了解決這一混淆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條對傳銷罪中的騙取財物進行了詳細說明:“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從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認定為騙取財物。”可見,傳銷罪中的“騙”是通過傳銷這種形式非法獲利。這一解釋與國務院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的規定相契合。可以說,刑法修正案(七)中規定的傳銷犯罪,在性質上屬于詐騙性傳銷,并不包括經營性傳銷。[3]通過上述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我們對集資詐騙中的“騙”與傳銷罪中的“騙”有了清晰的認識:二者雖然都有“騙”,但主觀目的不同。集資詐騙罪的“騙”,是以非法占有參加者的資金為目的;傳銷罪中的“騙”,是騙取他人加入傳銷組織,通過傳銷組織這種活動形式達到非法牟利的目的。
(三)由于兩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同,導致其對傳銷組織的態度以及所得錢款的去向等均有不同,實踐中可以成為區分兩罪的重要依據。如前所述,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傳銷犯罪的行為人是通過傳銷組織牟利,兩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同,導致其在行為上存在一定的差別。
1.兩罪行為人對待傳銷組織的態度不同。
對于集資詐騙的行為人來說,其目的是騙取集資款,建立傳銷組織對其來說只是一個手段。也許在集資初期,為了騙取更多的款項,其會向被害人支付一些利息,但一旦目的達到,行為人就會毫不猶疑地拋棄傳銷組織。但傳銷犯罪不同。對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來說,傳銷組織是他們盈利的保障,他們希望傳銷組織能長期發展下去。發展的規模越大,組織領導者的收益就越多。因此,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會想盡一切辦法維持傳銷組織一直存在發展下去,當一個傳銷組織已無力為繼,其組織、領導者往往會通過建立一個新組織來代替舊組織,以維持傳銷組織繼續發展。
2.行為人所得款項的去向不同。
集資詐騙行為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騙取集資款項占為己有,其騙得財物后,往往是通過轉移、隱匿、揮霍財產等方式,將集資款項非法占有。《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座談會紀要”)“關于金融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中,對實踐中如何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上述規定的表現形式雖各有不同,但本質上都是將被害人的財物據為己有,符合集資詐騙犯罪的主觀要件。
而在傳銷犯罪中,傳銷組織是行為人用來牟利的手段,傳銷組織存在的時間越長,其行為人的獲利就越多。傳銷組織者、領導者希望傳銷組織能長期發展下去,其會將所得的款項主要用于維持傳銷組織的運作,如給發展了下線的成員返利、支付傳銷組織的必要開支等等。傳銷犯罪的行為人通過組織會牟取一定的利益,但相比較來說,維持傳銷組織的開支必然更為龐大。維持傳銷組織運作,是傳銷行為人所得款項的主要去處。在座談會紀要中也明確規定,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傳銷犯罪之“罪”,在于傳銷組織形式非法,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并非行為人謀取利益。需要強調的是,由于金字塔式的傳銷模式發展下線迅速,涉及大量的人員及財產,傳銷犯罪的行為人往往也會有大量錢款不能返還,但僅憑這一點,不能認定行為人就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對此,座談會紀要中明確規定,要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借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集資詐騙罪處罰。
二、從集資詐騙罪和傳銷犯罪的組織形式看,二者有明顯區別。
對于集資詐騙行為人來說,其建立傳銷式組織的目的是騙取被害人財物。該組織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層層發展下線,對發展了下級的上級成員有一些獎勵,但這種組織與傳銷犯罪中的傳銷組織仍有不同。
(一)要分析兩罪中組織性質的不同。首先也要摒除一個誤區:以項目吸收投資就是集資詐騙,以商品吸收投資是傳銷犯罪。集資詐騙行為通常是通過偽造項目吸引投資,這是集資詐騙犯罪的慣用手法。而傳統的傳銷都是從實物商品開始,我們對于傳銷犯罪最直觀的理解就是以銷售實物商品的名義發展下線的行為。由此產生一種誤區:只有以商品、服務等作為傳銷內容的,才是傳銷活動;以項目為名義吸收他人投資,就是集資。但是,根據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并不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虛構項目的行為,就一定構成集資詐騙犯罪。虛構項目也是傳銷活動中的常用手段。傳銷罪司法解釋第3條規定,行為人“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的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構成傳銷罪。可見,并不是只要行為人虛構經營項目,就一定是集資詐騙。傳銷犯罪中,組織、領導行為的對象是傳銷活動而非傳銷組織,“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人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都是對傳銷活動的界定。[4]傳銷是一種牟利方式,具體內容是什么,行為人究竟構成集資詐騙還是傳銷犯罪,要根據其行為特征,結合法律規定各罪的構成要件,綜合判定。
(二)傳銷的內容不能成為區別兩罪的依據。實踐中可以從以下角度區分兩罪。
1.從參加者資格的必要性區分。
在傳銷活動中,參加者只有通過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獲得資格,才有可能通過發展下級來獲得收益。這種資格的確認,是組織、領導者通過制度、方案、體系等方式確定的。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構成傳銷犯罪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傳銷犯罪被害人的資格要件。而集資詐騙的被害人并不是必須獲得這種加入資格,說白了,集資詐騙行為人就是為了騙錢,只要能騙到錢,行為人對于被害人并沒有資格上的限制。我國刑法將集資詐騙罪的特征描述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等方式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行為”,被害人被騙不需要事先獲得所謂的資格。是否具備資格,是傳銷犯罪與集資詐騙犯罪的重要區別之一。
2.從活動組織是否具有層級性、剝削性區分。
從結構形式上,集資詐騙行為人與投資者都是直接聯絡,不存在層級限制,[5]是扁平式、輻射狀的。介紹新人投資,集資人可能會給介紹人獎勵,如張三介紹了李四,集資人對張三進行獎勵;李四介紹了王五,集資人又對李四進行獎勵,表面上看是不斷發展下線,但實際上并不形成“集資人—張三—李四—王五”之間的層級關系,而只是形成“集資人—李四”、“集資人—王五”這種集資人與參加者之間的直接關系。張三、李四、王五之間也并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推薦人的額外收益來源于集資行為人的獎勵,并非對被推薦人的剝削。傳銷則不同。傳銷犯罪是通過所謂的資本運作等經營活動來實現,其利益主要是靠發展下線拉人頭來實現;由于其組織結構往往體現出等級森嚴的層級結構,下線成員只與自己的上線成員單線聯系,不能突破層級限制。傳銷犯罪是金字塔式,具有明顯的層級關系,上級剝削下級,層層剝削。參加者在哪一層,也就決定了其會受到多少上層的剝削和對下層的剝削會有多少收益。參加者一般只能知道自己的下層有多少,這直接關系到自己的收益有多少。新會員在系統里的擺放位置原則上是由他的直接推薦人(上一層)決定的,因為新會員在系統里的擺放位置,直接影響到很多人的收益。這種層級性,也是區別兩罪的關鍵點之一。
3.從投資方案區別。
無論是集資還是傳銷組織,為了吸引投資人參加,都會設計一整套所謂的投資方案。從投資方案上,也可以看出行為人是集資詐騙還是傳銷牟利。集資詐騙案件中,不論行為人將所謂的項目或者投資方案描述得多么天花亂墜,本質上都屬于還本付息的性質。行為人會向被害人承諾在一定期限內或者達到一定條件后,連本帶利還給被害人,讓被害人獲得高額利息,以吸引被害人投資,騙取被害人的投資款。在傳銷犯罪中,組織領導者雖然也向參加者許諾高額收益,但收益的來源(或者說返利方案)基于參加者拉來下線的人數,是直接或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返利依據的。換句話說,根據傳銷犯罪的投資方案,參加者的主要獲利來源不是還本付息,而是按人計酬。綜上可見,即便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采用了傳銷的手段,看起來與傳銷犯罪雷同,但為服務于不同的犯罪目的,二罪中的傳銷組織仍然存在不同,實踐中可以成為區分兩罪的重要依據。
三、從行為人及組織參與者的角度看,兩罪有明顯區別。
(一)傳銷活動的發起者沒有直接發展下線,構成集資詐騙犯罪。由于傳銷活動的發起者、組織者并不直接發展下線,又吸收了大量的金錢,其行為后果看起來與集資詐騙罪的后果十分相似,導致實踐中容易產生這樣一個誤區:只有直接發展下線的人員才是傳銷,發起者沒有直接發展下線,其行為不構成傳銷犯罪,構成集資詐騙罪。這是兩罪在定性上容易產生的另一個誤區。任何傳銷活動都必然有發起者,并有相關的工作人員,發起者可能沒有直接發展下線,而是通過“地區領導人”、“網頭”等間接發展傳銷人員。但是,沒有直接發展下線并不影響該組織領導者的行為定性。根據傳銷罪司法解釋第2條第1款的規定,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承擔管理、協調、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以及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不論是直接發展下線,還是間接發展下線,都屬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依法都構成傳銷犯罪。該解釋第7條第3款規定:“對傳銷組織內部人數和層級數的計算,以及對組織者、領導者直接或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員人數和層級的計算,包括組織者、領導者本人及其本層級在內。”發起者、組織者處于傳銷組織的頂層,雖然其沒有直接發展下線,也同樣構成傳銷犯罪。任何一個傳銷組織都不可能沒有發起者,不能因為他們沒有直接發展下線,就認定構成集資詐騙犯罪。
(二)從參與者來看,兩罪組織的參與者有明顯不同。
1.參加者的動機及獲利來源不同。集資詐騙的被害人進行投資,是受他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而產生的錯誤認識,將集資款交給行為人,從而導致被騙。傳銷罪中的參加者,從實質上講,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被害人,其決定交易是受利益誘惑,并不是因為組織者虛構事實、行為誤導而產生錯誤認識。傳銷組織的獲利方案是固定的、公開的,參加者十分清楚自己的獲利模式。根據設計方案,自己投入多少,下線有多少,能夠獲利多少,一清二楚。雖然兩罪的參加者都希望獲利,但集資詐騙罪的被害人的獲利主要靠高額利息“錢生錢”,參加者的獲利與投資多少、期間長短密切相關。而傳銷活動的參與者是通過發展下線來獲利,通過“人生錢”,其獲利雖然也與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數量有關,但主要的獲利是自己能否發展更多的下線。如果參加者不能發展下線,或者發展下線的數量不足,則難以獲利,發展的層級和人數決定了參加者獲利收益。
2.傳銷活動的參加者可能轉換為傳銷組織的共犯,但集資詐騙活動的參與者一般不存在這種可能。在傳銷活動中,被利誘自愿加入傳銷組織并積極發展下線的參與者,實際上不能完全算傳銷犯罪的被害人。傳銷活動中除了頂層和最底層兩端之外,絕大多數的中間層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即便是最底層的參與者,如果傳銷組織能持續下去,其也會繼續發展下線,轉化為加害者。雖然傳銷犯罪針對的僅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但這個組織者、領導者的范疇要明顯大于傳銷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6]在傳銷犯罪中,除了位于“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幾個人外,積極參與傳銷組織,對于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參與者,都有可能會由被害人轉化為傳銷組織的共犯。而集資詐騙行為中,被害人就是純粹的被害人,即便被害人推薦了別的被害人,一般也不存在與集資詐騙人成為共犯的情況。傳銷罪司法解釋還規定了集資詐騙犯罪與傳銷犯罪的想象競合犯。要構成這一想象競合犯,則行為必須同時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及集資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僅符合一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則其行為不屬于想象競合犯,不能適用該規定,應當按照行為實際構成的罪名定罪處罰。需要強調的是,只有先認定行為人實施了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傳銷犯罪與集資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才能得出行為人構成想象競合犯的結論。
【注釋】 [1]張明楷:“傳銷犯罪的基本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9期。
[2]中國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5年度案例刑法分則案例》,中國法治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
[3]陳興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性質與界限(上)”,載《政法論壇》2016年第2期。
[4]高銘暄、趙秉志、黃曉亮、袁彬:“刑法修正案(七)罪名之研析(上)”,載2009年3月18日《法制日報》。
[5]付胥宇、武宇紅:“網絡傳銷犯罪適用罪名探討”,載《人民論壇》2014年第8期。
[6]周炳日、喻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適用疑難問題解析”,載《中國檢察官》2014年第8期。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下簡稱傳銷犯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構成集資詐騙罪。相比較來看,傳銷是一種非法的經營手段,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罪名之前,對于此種行為一直定性為非法經營罪,其主要侵犯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集資詐騙行為人實施的是非法集資行為,其主要侵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依法懲處非法集資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非法集資的主要特征有:一是未經有關監管部門依法批準,違規向社會(尤其是向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二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出資人貨幣、實務、股權等形式的投資回報;三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集資目的。由于傳銷組織往往發展迅速,能在短期內聚集大量的人員和款項,很多集資詐騙行為人往往采用傳銷式的組織形式來進行集資詐騙活動。正是由于這種“披著傳銷外衣的集資詐騙”情況的存在,導致對兩罪的認定極易產生混淆,特別是容易將傳銷犯罪通通誤認為是集資詐騙罪,產生種種誤解,例如,只要有欺騙行為就是集資詐騙、傳銷組織最頂層的發起者構成集資詐騙、傳銷項目的都是集資詐騙等誤區。事實上,即便集資詐騙行為人采用類似傳銷的方式,其與傳銷犯罪也存在一些本質上的區別,應將二者進行明確區分,以便正確定罪量刑。
(一)首先,要理解二罪之間主觀目的的差異性,必須先摒除一個錯誤的觀念:只有詐騙犯罪才具有欺騙性。集資詐騙罪與詐騙罪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集資詐騙罪同樣具有詐騙罪的重要特征—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為目的。也就是說,行為人的目的是直接侵害他人財產,將財產作為犯罪的對象。關于集資詐騙行為具有欺騙性,這毋庸置疑。也正因如此,極易產生一個誤區:只要用欺騙方法吸收投資人資金,就是集資詐騙罪。這種觀念是十分錯誤的:傳銷犯罪與集資詐騙犯罪均具有欺騙性,不能僅憑此來區分兩罪。事實上,并不是只有詐騙犯罪才具有欺騙性。行為具有欺騙性的犯罪還有虛假廣告罪、串通招投標罪等等。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傳銷是“……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可見,傳銷犯罪本身也具有欺騙性,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正是通過騙取參加者加人組織,以傳銷這種非法的組織形式來謀取利益的。可以說,騙取財物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傳銷活動的基本特征或者構成要件要素。[1]對于這一點,法律有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達成共識:在傳銷活動中,為了不斷發展人員加人,行為人通常用高額利潤作誘餌,夸大或虛構傭金或獎金收人,收取高額入門費或強制購買產品,這似乎具有某些詐騙罪的特征,但傳銷中參加者是追逐高額回報而加入其中的,其決定交易是受到利益的誘惑,而不是因虛構事實、行為誤導而產生的錯誤認識,故其行為不是受害者行為,不受法律保護。[2]可見,并不是只要通過欺騙方法吸引投資人投資,就構成集資詐騙犯罪,該行為同樣可以構成傳銷犯罪。
(二)傳銷犯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通過資格、層級等銷售模式謀取非法利益,而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騙取、非法占有他人財物。雖然集資詐騙罪與傳銷罪都具有欺騙性,但二者的“騙”是有區別的。傳銷罪是從直銷而來,直銷是一種銷售方式,即直銷企業招募直銷員,繞過傳統批發商或零售渠道,直接向最終消費者進行銷售。這種銷售方式在我國是必須經過批準的。而傳銷往往是披著直銷的外衣來吸引參加者以騙取財物。國務院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指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人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由此可見,傳銷是通過資格、層級、人員數量這種銷售模式牟取非法利益的行為,為國家所禁止。
由于刑法在傳銷罪的罪狀描述中使用了騙取財物一詞,致使司法實踐中往往將傳銷罪中騙取財物與集資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相混同。也就是說,將集資詐騙的“騙”,與傳銷罪中的“騙”相混同。為了解決這一混淆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條對傳銷罪中的騙取財物進行了詳細說明:“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從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認定為騙取財物。”可見,傳銷罪中的“騙”是通過傳銷這種形式非法獲利。這一解釋與國務院禁止傳銷條例第二條的規定相契合。可以說,刑法修正案(七)中規定的傳銷犯罪,在性質上屬于詐騙性傳銷,并不包括經營性傳銷。[3]通過上述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我們對集資詐騙中的“騙”與傳銷罪中的“騙”有了清晰的認識:二者雖然都有“騙”,但主觀目的不同。集資詐騙罪的“騙”,是以非法占有參加者的資金為目的;傳銷罪中的“騙”,是騙取他人加入傳銷組織,通過傳銷組織這種活動形式達到非法牟利的目的。
(三)由于兩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同,導致其對傳銷組織的態度以及所得錢款的去向等均有不同,實踐中可以成為區分兩罪的重要依據。如前所述,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傳銷犯罪的行為人是通過傳銷組織牟利,兩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同,導致其在行為上存在一定的差別。
1.兩罪行為人對待傳銷組織的態度不同。
對于集資詐騙的行為人來說,其目的是騙取集資款,建立傳銷組織對其來說只是一個手段。也許在集資初期,為了騙取更多的款項,其會向被害人支付一些利息,但一旦目的達到,行為人就會毫不猶疑地拋棄傳銷組織。但傳銷犯罪不同。對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來說,傳銷組織是他們盈利的保障,他們希望傳銷組織能長期發展下去。發展的規模越大,組織領導者的收益就越多。因此,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會想盡一切辦法維持傳銷組織一直存在發展下去,當一個傳銷組織已無力為繼,其組織、領導者往往會通過建立一個新組織來代替舊組織,以維持傳銷組織繼續發展。
2.行為人所得款項的去向不同。
集資詐騙行為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騙取集資款項占為己有,其騙得財物后,往往是通過轉移、隱匿、揮霍財產等方式,將集資款項非法占有。《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座談會紀要”)“關于金融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中,對實踐中如何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上述規定的表現形式雖各有不同,但本質上都是將被害人的財物據為己有,符合集資詐騙犯罪的主觀要件。
而在傳銷犯罪中,傳銷組織是行為人用來牟利的手段,傳銷組織存在的時間越長,其行為人的獲利就越多。傳銷組織者、領導者希望傳銷組織能長期發展下去,其會將所得的款項主要用于維持傳銷組織的運作,如給發展了下線的成員返利、支付傳銷組織的必要開支等等。傳銷犯罪的行為人通過組織會牟取一定的利益,但相比較來說,維持傳銷組織的開支必然更為龐大。維持傳銷組織運作,是傳銷行為人所得款項的主要去處。在座談會紀要中也明確規定,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便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傳銷犯罪之“罪”,在于傳銷組織形式非法,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并非行為人謀取利益。需要強調的是,由于金字塔式的傳銷模式發展下線迅速,涉及大量的人員及財產,傳銷犯罪的行為人往往也會有大量錢款不能返還,但僅憑這一點,不能認定行為人就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對此,座談會紀要中明確規定,要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借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單純以財產不能歸還就按集資詐騙罪處罰。
二、從集資詐騙罪和傳銷犯罪的組織形式看,二者有明顯區別。
對于集資詐騙行為人來說,其建立傳銷式組織的目的是騙取被害人財物。該組織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層層發展下線,對發展了下級的上級成員有一些獎勵,但這種組織與傳銷犯罪中的傳銷組織仍有不同。
(一)要分析兩罪中組織性質的不同。首先也要摒除一個誤區:以項目吸收投資就是集資詐騙,以商品吸收投資是傳銷犯罪。集資詐騙行為通常是通過偽造項目吸引投資,這是集資詐騙犯罪的慣用手法。而傳統的傳銷都是從實物商品開始,我們對于傳銷犯罪最直觀的理解就是以銷售實物商品的名義發展下線的行為。由此產生一種誤區:只有以商品、服務等作為傳銷內容的,才是傳銷活動;以項目為名義吸收他人投資,就是集資。但是,根據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并不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虛構項目的行為,就一定構成集資詐騙犯罪。虛構項目也是傳銷活動中的常用手段。傳銷罪司法解釋第3條規定,行為人“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的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構成傳銷罪。可見,并不是只要行為人虛構經營項目,就一定是集資詐騙。傳銷犯罪中,組織、領導行為的對象是傳銷活動而非傳銷組織,“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人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都是對傳銷活動的界定。[4]傳銷是一種牟利方式,具體內容是什么,行為人究竟構成集資詐騙還是傳銷犯罪,要根據其行為特征,結合法律規定各罪的構成要件,綜合判定。
(二)傳銷的內容不能成為區別兩罪的依據。實踐中可以從以下角度區分兩罪。
1.從參加者資格的必要性區分。
在傳銷活動中,參加者只有通過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獲得資格,才有可能通過發展下級來獲得收益。這種資格的確認,是組織、領導者通過制度、方案、體系等方式確定的。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構成傳銷犯罪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傳銷犯罪被害人的資格要件。而集資詐騙的被害人并不是必須獲得這種加入資格,說白了,集資詐騙行為人就是為了騙錢,只要能騙到錢,行為人對于被害人并沒有資格上的限制。我國刑法將集資詐騙罪的特征描述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等方式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行為”,被害人被騙不需要事先獲得所謂的資格。是否具備資格,是傳銷犯罪與集資詐騙犯罪的重要區別之一。
2.從活動組織是否具有層級性、剝削性區分。
從結構形式上,集資詐騙行為人與投資者都是直接聯絡,不存在層級限制,[5]是扁平式、輻射狀的。介紹新人投資,集資人可能會給介紹人獎勵,如張三介紹了李四,集資人對張三進行獎勵;李四介紹了王五,集資人又對李四進行獎勵,表面上看是不斷發展下線,但實際上并不形成“集資人—張三—李四—王五”之間的層級關系,而只是形成“集資人—李四”、“集資人—王五”這種集資人與參加者之間的直接關系。張三、李四、王五之間也并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推薦人的額外收益來源于集資行為人的獎勵,并非對被推薦人的剝削。傳銷則不同。傳銷犯罪是通過所謂的資本運作等經營活動來實現,其利益主要是靠發展下線拉人頭來實現;由于其組織結構往往體現出等級森嚴的層級結構,下線成員只與自己的上線成員單線聯系,不能突破層級限制。傳銷犯罪是金字塔式,具有明顯的層級關系,上級剝削下級,層層剝削。參加者在哪一層,也就決定了其會受到多少上層的剝削和對下層的剝削會有多少收益。參加者一般只能知道自己的下層有多少,這直接關系到自己的收益有多少。新會員在系統里的擺放位置原則上是由他的直接推薦人(上一層)決定的,因為新會員在系統里的擺放位置,直接影響到很多人的收益。這種層級性,也是區別兩罪的關鍵點之一。
3.從投資方案區別。
無論是集資還是傳銷組織,為了吸引投資人參加,都會設計一整套所謂的投資方案。從投資方案上,也可以看出行為人是集資詐騙還是傳銷牟利。集資詐騙案件中,不論行為人將所謂的項目或者投資方案描述得多么天花亂墜,本質上都屬于還本付息的性質。行為人會向被害人承諾在一定期限內或者達到一定條件后,連本帶利還給被害人,讓被害人獲得高額利息,以吸引被害人投資,騙取被害人的投資款。在傳銷犯罪中,組織領導者雖然也向參加者許諾高額收益,但收益的來源(或者說返利方案)基于參加者拉來下線的人數,是直接或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返利依據的。換句話說,根據傳銷犯罪的投資方案,參加者的主要獲利來源不是還本付息,而是按人計酬。綜上可見,即便集資詐騙犯罪行為人采用了傳銷的手段,看起來與傳銷犯罪雷同,但為服務于不同的犯罪目的,二罪中的傳銷組織仍然存在不同,實踐中可以成為區分兩罪的重要依據。
三、從行為人及組織參與者的角度看,兩罪有明顯區別。
(一)傳銷活動的發起者沒有直接發展下線,構成集資詐騙犯罪。由于傳銷活動的發起者、組織者并不直接發展下線,又吸收了大量的金錢,其行為后果看起來與集資詐騙罪的后果十分相似,導致實踐中容易產生這樣一個誤區:只有直接發展下線的人員才是傳銷,發起者沒有直接發展下線,其行為不構成傳銷犯罪,構成集資詐騙罪。這是兩罪在定性上容易產生的另一個誤區。任何傳銷活動都必然有發起者,并有相關的工作人員,發起者可能沒有直接發展下線,而是通過“地區領導人”、“網頭”等間接發展傳銷人員。但是,沒有直接發展下線并不影響該組織領導者的行為定性。根據傳銷罪司法解釋第2條第1款的規定,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承擔管理、協調、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以及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不論是直接發展下線,還是間接發展下線,都屬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依法都構成傳銷犯罪。該解釋第7條第3款規定:“對傳銷組織內部人數和層級數的計算,以及對組織者、領導者直接或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員人數和層級的計算,包括組織者、領導者本人及其本層級在內。”發起者、組織者處于傳銷組織的頂層,雖然其沒有直接發展下線,也同樣構成傳銷犯罪。任何一個傳銷組織都不可能沒有發起者,不能因為他們沒有直接發展下線,就認定構成集資詐騙犯罪。
(二)從參與者來看,兩罪組織的參與者有明顯不同。
1.參加者的動機及獲利來源不同。集資詐騙的被害人進行投資,是受他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而產生的錯誤認識,將集資款交給行為人,從而導致被騙。傳銷罪中的參加者,從實質上講,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被害人,其決定交易是受利益誘惑,并不是因為組織者虛構事實、行為誤導而產生錯誤認識。傳銷組織的獲利方案是固定的、公開的,參加者十分清楚自己的獲利模式。根據設計方案,自己投入多少,下線有多少,能夠獲利多少,一清二楚。雖然兩罪的參加者都希望獲利,但集資詐騙罪的被害人的獲利主要靠高額利息“錢生錢”,參加者的獲利與投資多少、期間長短密切相關。而傳銷活動的參與者是通過發展下線來獲利,通過“人生錢”,其獲利雖然也與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數量有關,但主要的獲利是自己能否發展更多的下線。如果參加者不能發展下線,或者發展下線的數量不足,則難以獲利,發展的層級和人數決定了參加者獲利收益。
2.傳銷活動的參加者可能轉換為傳銷組織的共犯,但集資詐騙活動的參與者一般不存在這種可能。在傳銷活動中,被利誘自愿加入傳銷組織并積極發展下線的參與者,實際上不能完全算傳銷犯罪的被害人。傳銷活動中除了頂層和最底層兩端之外,絕大多數的中間層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即便是最底層的參與者,如果傳銷組織能持續下去,其也會繼續發展下線,轉化為加害者。雖然傳銷犯罪針對的僅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但這個組織者、領導者的范疇要明顯大于傳銷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6]在傳銷犯罪中,除了位于“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幾個人外,積極參與傳銷組織,對于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參與者,都有可能會由被害人轉化為傳銷組織的共犯。而集資詐騙行為中,被害人就是純粹的被害人,即便被害人推薦了別的被害人,一般也不存在與集資詐騙人成為共犯的情況。傳銷罪司法解釋還規定了集資詐騙犯罪與傳銷犯罪的想象競合犯。要構成這一想象競合犯,則行為必須同時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及集資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僅符合一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則其行為不屬于想象競合犯,不能適用該規定,應當按照行為實際構成的罪名定罪處罰。需要強調的是,只有先認定行為人實施了一個行為、同時符合傳銷犯罪與集資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才能得出行為人構成想象競合犯的結論。
【注釋】 [1]張明楷:“傳銷犯罪的基本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9期。
[2]中國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5年度案例刑法分則案例》,中國法治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
[3]陳興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性質與界限(上)”,載《政法論壇》2016年第2期。
[4]高銘暄、趙秉志、黃曉亮、袁彬:“刑法修正案(七)罪名之研析(上)”,載2009年3月18日《法制日報》。
[5]付胥宇、武宇紅:“網絡傳銷犯罪適用罪名探討”,載《人民論壇》2014年第8期。
[6]周炳日、喻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適用疑難問題解析”,載《中國檢察官》2014年第8期。
還有70%,馬上登錄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