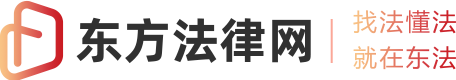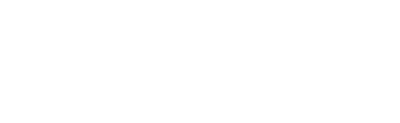解除同居關系糾紛案件的法律問題
- 期刊名稱:《人民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第5條,對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法院要求離婚的,是作為事實婚姻還是同居關系處理,按時限作了明確界定。這里所稱的同居關系,是被賦予特定涵義的一種新提法。本文通過對一起具體案例的分析,揭示同居關系的新內涵,并對解除同居關系案件的審理程序和實體處理等相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田某(男)與鄒某(女)同系四川省宜賓縣農民。二人于1998年12月經人介紹建立戀愛關系,于1999年3月一同赴北京打工。在打工期間,雙方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不久鄒某懷孕。因鄒某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在到京一月后即返回宜賓縣老家,并在家人陪同下到醫院實施了人工流產手術。2000年1月,田某與鄒某按民間風俗習慣舉行了婚禮,鄒某帶著被蓋等嫁妝到田某家生活,但雙方一直未到鄉政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同年8月,鄒某出現精神異常現象,經診斷為分裂樣精神病。其后,田某以與鄒某性格不合、生活痛苦等為由向宜賓縣法院起訴,請求與鄒某“離婚”。鄒某以要求田某給付精神病醫療費和補助費等為由進行答辯。法院認為,田某與鄒某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便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其同居關系依法應予解除。鄒某患有精神疾病,應由田某對其進行經濟扶助。鄒某帶至田某家的嫁妝屬個人財產,歸鄒某所有。判決如下:1.解除田某與鄒某之間的同居關系;2.由田某一次性給付鄒某扶助費4032元;3.鄒某的被蓋等嫁妝歸鄒某所有。
同居關系的新涵義
田某與鄒某未依照婚姻法的規定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便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按《解釋》應屬同居關系。廣義的同居,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指男女雙方依法經婚姻登記建立夫妻關系而同居生活;二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生活;三是指男女雙方均無配偶,未經婚姻登記便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解釋》所稱的解除同居關系中的“同居”概念,單指前述第三種情況,是一種狹義的概念。為便于正確理解和適用《解釋》關于同居關系的規定,有必要就我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從對事實婚姻的有條件承認到全面否認并認定為同居關系的歷史沿革進行回顧,通過分析同居關系的法律特征,繼而深入理解同居關系這一特定法律概念的新內涵。
隨著我國現代婚姻家庭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對未經婚姻登記便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這種情況,有關司法解釋先后作出了三種不同規定,相應出現了事實婚姻、非法同居關系、同居關系三個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在1979年2月2日制定的《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見》中,對事實婚姻第一次下了定義,即:“事實婚姻是指沒有配偶的男女,未進行婚姻登記,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的。”根據這一意見,事實婚姻當事人起訴的離婚案件,在實體處理上,即準予離婚或不準離婚的標準上,與法律婚姻當事人起訴的離婚案件等同起來,結束了凡事實婚姻當事人一方起訴離婚,人民法院即準予離婚的歷史。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提出了非法同居關系這一概念。對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之后,未辦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但同居時雙方或一方未達法定條件的,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人民法院審理非法同居關系案件應一律判決予以解除;如同居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認定為事實婚姻;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日起,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無論其同居時是否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一律按非法同居關系對待。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釋》,取締了非法同居關系這一提法,將該類案件定義為解除同居關系糾紛。
同居關系的提法較之非法同居關系的提法更為規范和科學。后者以非法二字突出了這種關系的違法性,但易使人產生法律概念的混淆。一是可能使人誤認為與之相對的其他同居關系都是合法的,而事實上前述基于事實婚姻的同居和已婚者與第三者同居也屬違法;二是在法律適用上,有的審判人員易于基于對這種關系的非法性映象,在解除雙方的同居關系時,忽視保護同居者的財產權等合法權益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權利等。《解釋》關于同居關系的提法,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了這種關系的特征,有利于審判者和當事人正確理解和對待這種關系。筆者認為,《解釋》規定的同居關系有以下法律特征:1.這種同居關系有別于基于合法婚姻而產生的同居關系,違法性是其主要特征;2.同居關系建立在無配偶的男女之間,不同于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關系;3.同居關系須為男女雙方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4.同居時間較長,具有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的特征。本案原告田某和被告鄒某自1999年一直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而同居生活,實際上向社會公開了夫妻關系,且具有同居時間長、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的特征,符合同居關系的構成要件。
審理程序和實體處理
《解釋》對同居關系和事實婚姻的法律界定作了新的概括,即:“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發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發布實施以后,男女雙方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有關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和撫養問題,也由婚姻法第二十五條作出規定。但《解釋》對解除同居關系案件的案由、裁判方式、財產分割和債務清償等問題未予明確。根據法律精神和審判實踐經驗,筆者在此談談個人的意見。
案由確定。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在婚姻家庭糾紛部分確定了“解除非法同居關系糾紛”這一案由,按《解釋》的精神,應修正為“解除同居關系糾紛”才準確。這一案由特指無配偶者未辦結婚登記便以夫妻名義同居而發生的解除同居關系糾紛,這樣規定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將有配偶者與他人持續、穩定地同居與此相混淆。在判決結果上,應改變過去“解除雙方的非法同居關系”的寫法,將新案由表述為“解除雙方的同居關系”才為規范。當然,在判決書“審理認為”部分,可以對同居關系的違法性進行闡述,為其后的實體判決打下說理基礎。
裁判方式。同居關系的違法性特征決定了對該類案件應適用特別的裁判方式,即人民法院只能適用判決或二審撤訴這兩種方式結案。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精神,調解以合法原則為基礎。前面已談到,同居關系具有違法性特征,因此對同居關系糾紛的人身關系解除部分不應進行調解,只能判決予以解除。二審撤回上訴的法律后果是雙方當事人均按一審判決執行,如果上訴人申請撤回上訴,符合法律規定的,應予準許。對于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分割,雖不提倡調解,但雙方當事人可以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一致,以判決形式確認雙方達成的財產分割協議。
財產分割和債務分擔。在同居期間,如果同居雙方得到財產并共同使用,在審理中必然涉及到對這一部分財產的分割問題。對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應根據其來源分別對待,不應按一般民商事案件處置非法所得財產的原則而予以收繳、沒收。學術界較為認同的“合伙說”認為,同居期間所得財產好似男女雙方在經濟上的合伙關系,在雙方解除同居關系時,除屬于一方所有的財產外,對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應參照合伙共有財產清算分割。筆者也認同這一觀點。參照婚姻法的精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同居一方所有的財產:1.一方同居前的財產;2.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3.一方在同居期間接受遺囑或贈與所得財產;4.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等。參照“合伙說”和婚姻法的精神,同居雙方均有權分得同居期間所得的共有財產。對于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商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關于同居雙方的繼承權問題,因為雙方不具有合法的婚姻關系,除了雙方因近親屬關系的特殊情況而依繼承法的規定享有繼承權外,雙方互無繼承對方遺產的權利。在解除同居關系時,如一方生活困難或存在其他必須接受扶助的情形,可判決另一方向其支付扶助費。對于同居期間所欠債務,專用于一方生產、生活的債務應由借債人單方償還,共同所負債務以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清償,不足部分由同居雙方對外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田某(男)與鄒某(女)同系四川省宜賓縣農民。二人于1998年12月經人介紹建立戀愛關系,于1999年3月一同赴北京打工。在打工期間,雙方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不久鄒某懷孕。因鄒某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在到京一月后即返回宜賓縣老家,并在家人陪同下到醫院實施了人工流產手術。2000年1月,田某與鄒某按民間風俗習慣舉行了婚禮,鄒某帶著被蓋等嫁妝到田某家生活,但雙方一直未到鄉政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同年8月,鄒某出現精神異常現象,經診斷為分裂樣精神病。其后,田某以與鄒某性格不合、生活痛苦等為由向宜賓縣法院起訴,請求與鄒某“離婚”。鄒某以要求田某給付精神病醫療費和補助費等為由進行答辯。法院認為,田某與鄒某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便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其同居關系依法應予解除。鄒某患有精神疾病,應由田某對其進行經濟扶助。鄒某帶至田某家的嫁妝屬個人財產,歸鄒某所有。判決如下:1.解除田某與鄒某之間的同居關系;2.由田某一次性給付鄒某扶助費4032元;3.鄒某的被蓋等嫁妝歸鄒某所有。
同居關系的新涵義
田某與鄒某未依照婚姻法的規定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便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按《解釋》應屬同居關系。廣義的同居,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指男女雙方依法經婚姻登記建立夫妻關系而同居生活;二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生活;三是指男女雙方均無配偶,未經婚姻登記便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解釋》所稱的解除同居關系中的“同居”概念,單指前述第三種情況,是一種狹義的概念。為便于正確理解和適用《解釋》關于同居關系的規定,有必要就我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從對事實婚姻的有條件承認到全面否認并認定為同居關系的歷史沿革進行回顧,通過分析同居關系的法律特征,繼而深入理解同居關系這一特定法律概念的新內涵。
隨著我國現代婚姻家庭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對未經婚姻登記便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這種情況,有關司法解釋先后作出了三種不同規定,相應出現了事實婚姻、非法同居關系、同居關系三個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在1979年2月2日制定的《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見》中,對事實婚姻第一次下了定義,即:“事實婚姻是指沒有配偶的男女,未進行婚姻登記,以夫妻關系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的。”根據這一意見,事實婚姻當事人起訴的離婚案件,在實體處理上,即準予離婚或不準離婚的標準上,與法律婚姻當事人起訴的離婚案件等同起來,結束了凡事實婚姻當事人一方起訴離婚,人民法院即準予離婚的歷史。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提出了非法同居關系這一概念。對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之后,未辦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但同居時雙方或一方未達法定條件的,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人民法院審理非法同居關系案件應一律判決予以解除;如同居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認定為事實婚姻;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日起,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無論其同居時是否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一律按非法同居關系對待。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釋》,取締了非法同居關系這一提法,將該類案件定義為解除同居關系糾紛。
同居關系的提法較之非法同居關系的提法更為規范和科學。后者以非法二字突出了這種關系的違法性,但易使人產生法律概念的混淆。一是可能使人誤認為與之相對的其他同居關系都是合法的,而事實上前述基于事實婚姻的同居和已婚者與第三者同居也屬違法;二是在法律適用上,有的審判人員易于基于對這種關系的非法性映象,在解除雙方的同居關系時,忽視保護同居者的財產權等合法權益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權利等。《解釋》關于同居關系的提法,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了這種關系的特征,有利于審判者和當事人正確理解和對待這種關系。筆者認為,《解釋》規定的同居關系有以下法律特征:1.這種同居關系有別于基于合法婚姻而產生的同居關系,違法性是其主要特征;2.同居關系建立在無配偶的男女之間,不同于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關系;3.同居關系須為男女雙方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4.同居時間較長,具有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的特征。本案原告田某和被告鄒某自1999年一直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而同居生活,實際上向社會公開了夫妻關系,且具有同居時間長、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的特征,符合同居關系的構成要件。
審理程序和實體處理
《解釋》對同居關系和事實婚姻的法律界定作了新的概括,即:“未按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到人民法院要求離婚的,應當區別對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發布實施以前,男女雙方已經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按事實婚姻處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發布實施以后,男女雙方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補辦結婚登記;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有關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和撫養問題,也由婚姻法第二十五條作出規定。但《解釋》對解除同居關系案件的案由、裁判方式、財產分割和債務清償等問題未予明確。根據法律精神和審判實踐經驗,筆者在此談談個人的意見。
案由確定。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在婚姻家庭糾紛部分確定了“解除非法同居關系糾紛”這一案由,按《解釋》的精神,應修正為“解除同居關系糾紛”才準確。這一案由特指無配偶者未辦結婚登記便以夫妻名義同居而發生的解除同居關系糾紛,這樣規定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將有配偶者與他人持續、穩定地同居與此相混淆。在判決結果上,應改變過去“解除雙方的非法同居關系”的寫法,將新案由表述為“解除雙方的同居關系”才為規范。當然,在判決書“審理認為”部分,可以對同居關系的違法性進行闡述,為其后的實體判決打下說理基礎。
裁判方式。同居關系的違法性特征決定了對該類案件應適用特別的裁判方式,即人民法院只能適用判決或二審撤訴這兩種方式結案。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精神,調解以合法原則為基礎。前面已談到,同居關系具有違法性特征,因此對同居關系糾紛的人身關系解除部分不應進行調解,只能判決予以解除。二審撤回上訴的法律后果是雙方當事人均按一審判決執行,如果上訴人申請撤回上訴,符合法律規定的,應予準許。對于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分割,雖不提倡調解,但雙方當事人可以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一致,以判決形式確認雙方達成的財產分割協議。
財產分割和債務分擔。在同居期間,如果同居雙方得到財產并共同使用,在審理中必然涉及到對這一部分財產的分割問題。對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應根據其來源分別對待,不應按一般民商事案件處置非法所得財產的原則而予以收繳、沒收。學術界較為認同的“合伙說”認為,同居期間所得財產好似男女雙方在經濟上的合伙關系,在雙方解除同居關系時,除屬于一方所有的財產外,對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應參照合伙共有財產清算分割。筆者也認同這一觀點。參照婚姻法的精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同居一方所有的財產:1.一方同居前的財產;2.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3.一方在同居期間接受遺囑或贈與所得財產;4.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等。參照“合伙說”和婚姻法的精神,同居雙方均有權分得同居期間所得的共有財產。對于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商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照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關于同居雙方的繼承權問題,因為雙方不具有合法的婚姻關系,除了雙方因近親屬關系的特殊情況而依繼承法的規定享有繼承權外,雙方互無繼承對方遺產的權利。在解除同居關系時,如一方生活困難或存在其他必須接受扶助的情形,可判決另一方向其支付扶助費。對于同居期間所欠債務,專用于一方生產、生活的債務應由借債人單方償還,共同所負債務以同居期間所得財產清償,不足部分由同居雙方對外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還有70%,馬上登錄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