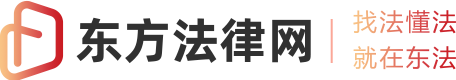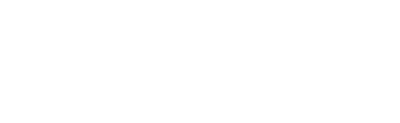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構成要件的再探析
- 期刊名稱:《法制與社會》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構成要件的再探析
蔡鶯依
摘要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其直接侵犯的客體為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秩序;客觀方面包括幫助行為、幫助時限等內容,部分內容在理論上學者們還尚未能夠達成共識,必須予以深入探討和分析;主體范圍是排除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之外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單位、當事人不能成為本罪主體;主觀方面只能表現為故意的犯罪心理狀態,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正確適用關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相關規定,對該行為予以規制和調整。
關鍵詞 犯罪故意 犯罪動機 期待可能性 教唆犯
作者簡介:蔡鶯依,浙江農林大學法學專業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410
一、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客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7條第2款規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從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侵犯的客體來看,其直接侵犯了我國正常的司法秩序。而且,由于這類行為的存在嚴重的影響了我國正常的司法秩序,尤其是訴訟活動的正常秩序,因而往往會導致二審、再審等訴訟活動的啟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當事人訴累,也導致原本就稀少的司法資源的浪費。
此外,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犯罪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還會間接的侵害其他合法權益。例如,行為人為了幫助他人逃避法律制裁,而實施了“偽造證據”的行為,將犯罪嫁禍于他人導致他人被追究法律責任,嚴重的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所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所侵犯的客體種類較多,其社會危害性較大,但是是否就能簡單將本罪客體理解為復雜客體呢?從復雜客體的定義來看,必須要某種犯罪行為同時直接侵犯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具體社會關系,才能說某種犯罪行為侵犯了復雜客體。而從幫助毀滅、偽造證據所直接侵犯的客體來看,其直接侵犯的客體只有正常的司法活動秩序,因而,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侵犯的客體應當是簡單客體,而非復雜客體。
二、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客觀方面
(一)“幫助”的對象“當事人”應作廣義解釋
根據我國《刑法》第307條第2款之規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對象為當事人,在此我們應當根據訴訟法的相關理論,對“當事人”的內涵采廣義的理解,該“當事人”既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活動當中的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等,也應當包括附帶民事訴訟當中的被告人及原告,且在民事、行政訴訟活動當中的原告和被告也應當納入該范疇之內,從廣義的角度對該罪名當中的“當事人”進行解釋也與立法初衷相符。
(二)“幫助”行為具體內容之“毀滅、偽造證據”
“毀滅證據”即妨礙證據出現,導致有證明力的證據無法出現在訴訟活動當中。例如,燒毀、撕爛、腐蝕證據等,使得證據形式被毀滅,也包括證據形態的喪失,如涂改等行為;“偽造證據”則是通過編制等方式導致原本沒有的證據出現或者對現有的證據予以整理、加工、篡改,導致其證明內容與爭先不符。上述行為都是行為人為了妨礙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通過使證據的證明力降低甚至消失,來避免真實證據在訴訟活動當中發揮其積極的證明力。
(三)“幫助”行為所直接作用之“證據”應作廣義解釋
對于“幫助”行為所直接作用的證據應當采廣義解釋的觀點予以理解,既包括已經被查證屬實的證據,也應當包括證據資料或者其原始素材。但是,其形式應當限定于鑒定結論、書證、已經書面化或者已經轉化為視聽資料形式的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等形式,而不應過于進行擴大解釋。
(四)“幫助”行為不僅可在訴訟活動之中,也可以在訴訟活動啟動之前
根據我國《刑法》第307條第2款之規定,被幫助的對象為“當事人”,那這是否說明,幫助行為也只能是在訴訟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實施呢?若給予上述問題肯定回答,顯然是有違司法公正的。正如前文所述,對于“當事人”的概念和內涵范疇我們應當運用訴訟法理論采廣義的看點,并不僅僅包括訴訟活動主體,所以,“幫助”行為并非以訴訟活動的開始為前提。所以,幫助行為既可以發生在訴訟活動過程之中,也同樣可以發生于訴訟活動啟動之前。
(五)“幫助”并不以被幫助人有犯罪行為為前提
“幫助”的行為是否需要以被幫助人的行為屬于犯罪行為作為其行為定性的前提?當前,理論界關于該問題產生了分歧。部分學者認為,幫助人的“幫助行為”以“被幫助人的犯罪為前提”或者“以被幫助人的違法犯罪為前提”,否則該“幫助”行為顯然也不應當構成犯罪。但是,也有部分學者持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幫助”的行為并不是以幫助人的行為屬于犯罪行為為前提,換言之,只要被幫助人的行為涉嫌犯罪,其“幫助”行為即成立。筆者更贊同后者觀點。正如前文關于訴訟時限的描述可以看出,“幫助行為”可以貫穿于訴訟活動之中,而被幫助人的行為唯有經過司法審判才能對其行為予以定性,因此,只要被幫助人的行為涉嫌犯罪,其“幫助”行為即成立。
(六)“幫助”行為須達到“情節嚴重”方可定罪
本罪屬于情節犯,唯有當事人的行為的情節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才可以適用本罪的相關規定對其追究刑事責任,換言之,若行為人具有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但是其行為尚不足以達到嚴重程度的,則不適用《刑法》對其行為追究刑事責任。
三、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主體
(一)本罪主體為自然人一般主體,單位不能成為本罪主體
根據我國刑法之規定,本罪的犯罪主體是指排除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以外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因而不難看出,單位不能成為本罪的犯罪主體,此外,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具有上述行為時適用《刑法》第306條規定的妨害作證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盡管,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5條之規定,單位作為主體由偽造證據、毀滅證據等行為的應當追究法律責任,但是我國刑法尚未就單位具有偽造證據、毀滅證據的行為進行規范,根據罪刑法定的原則,單位尚不能構成本罪的犯罪主體。
(二)當事人不能成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主體
根據德國“癖馬案”的期待可能性理論,同樣可以適用于考究當事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究竟是否觸碰刑律。當事人在實施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時,為掩蓋其犯罪事實所作出的一系列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所以,從期待可能性的理論角度來看,當事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不應當再予以刑事懲罰,當事人不能構成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罪的本罪主體。
(三)當事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不能成為本罪教唆犯
當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當中都未能針對當事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能不能成為本罪教唆犯的問題達成統一意見。以德國刑法為代表的立法例對于上述問題持肯定意見,但是,也有很多國家尚未就上述問題出臺立法予以明文立法規定,甚至在這些國家,肯定說與否定說并行。筆者認為,當事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不能成為本罪教唆犯,第一,考慮到相較于當事人自己直接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而言,其教唆他人偽造、毀滅證據的行為顯然社會危害性更輕,而若對于前者的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而對后者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顯然是自相矛盾的。第二,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是行為自己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還是教唆他人實施上述行為,由于都不具備期待可能性,所以當事人無法成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犯罪主體。
四、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主觀方面
我國刑法中將幫助、毀滅證據的行為認定為故意犯罪,該故意不僅僅包括行為人明知其為證據而進行幫助當事人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的直接故意,也應當包括行為人明知其為證據而采取基于其他原因而實施犯罪行為并對其可能給司法活動的客觀公正性造成的影響持放任的態度的間接故意。
(一)須正確區分犯罪動機與犯罪故意
對于偽造證據罪來講,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動機在實踐中常常存在難以區分的情況。首先,犯罪動機一般不影響案件的定性,只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其次,我們要注意的是本罪的犯罪動機具有多樣性,除了是當事人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之外,還有其他可以成立本罪的動機。而對于行為人是否有幫助當事人逃避或減輕法律責任的希望或者其他動機,則不會影響本罪的成立;最后,從立法的角度上出發,法律要制裁這種嚴重妨礙正常法律秩序的行為。行為人這種明知其行為是在幫助犯罪嫌疑人毀滅、偽造證據,并對偵查機關的正常偵查活動造成妨礙的情況下,仍然毀滅或偽造證據,其行為會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故應對其這種主觀故意、客觀危害的行為進行懲罰。
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實踐當中,不能夠片面的關注在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明知其行為是在幫助當事人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這一動機上,否則將很容易導致行為人否認這一幫助當事人逃避或減輕法律責任的動機從而不能夠使其入罪。倘若行為人是在不知道他人已經實施了犯罪行為,亦不知其行為使有關之證據被毀滅或改變,但是客觀上卻存在著妨礙司法取證的行為,對于這種行為筆者認為不應當包括在本罪之中。
(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筆者翻閱我國國內刑法學書籍以及相關著作發現,我國理論界對于本罪的主觀方面認定都是故意,但是并未對本罪的故意屬于主觀故意還是屬于間接故意做出明確界定,因此理論界在對本罪的主觀方面存在著爭論。筆者對本罪應包括間接故意持認同態度。所謂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當中,有許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案件都是以不作為的行為而體現的。例如旅館老板和清潔員工在客房內發現一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體時,即使旅館老板未對該清潔員工下達清理現場、轉移尸體的命令,而是對于清潔員工毀滅證據的行為不聞不問、不加阻止,但其作為一名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對于事物有正常的辨別能力,應當知道清理房間和轉移尸體是對刑事證據的毀壞,從而導致司法機關在案件偵破中存在困難,但其仍然對清潔員工的毀滅證據行為采取聽之任之的放任態度,以不作為的方式觸犯本罪,若在此情況下仍舊將本罪的主觀方面限于直接故意的話,就會使得這種妨礙司法秩序的行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使得犯罪分子逍遙法外,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所以,為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對犯罪分子更好的制裁,本罪的故意應當既包含行為人希望當事人逃避或減輕法律責任的直接故意,也包含行為人對毀壞、偽造證據從而妨礙司法偵查活動的間接故意。
參考文獻:
[1]鮮鐵可.妨害司法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2]陳正沓.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認定中的疑難問題探析.政治與法律.2003(4).
[3]張明楷.論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山東審判.2007(1).
[4][德]德國刑法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5]李希慧.刑法解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5.
蔡鶯依
摘要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其直接侵犯的客體為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秩序;客觀方面包括幫助行為、幫助時限等內容,部分內容在理論上學者們還尚未能夠達成共識,必須予以深入探討和分析;主體范圍是排除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之外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單位、當事人不能成為本罪主體;主觀方面只能表現為故意的犯罪心理狀態,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正確適用關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相關規定,對該行為予以規制和調整。
關鍵詞 犯罪故意 犯罪動機 期待可能性 教唆犯
作者簡介:蔡鶯依,浙江農林大學法學專業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410
一、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客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7條第2款規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從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侵犯的客體來看,其直接侵犯了我國正常的司法秩序。而且,由于這類行為的存在嚴重的影響了我國正常的司法秩序,尤其是訴訟活動的正常秩序,因而往往會導致二審、再審等訴訟活動的啟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當事人訴累,也導致原本就稀少的司法資源的浪費。
此外,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犯罪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還會間接的侵害其他合法權益。例如,行為人為了幫助他人逃避法律制裁,而實施了“偽造證據”的行為,將犯罪嫁禍于他人導致他人被追究法律責任,嚴重的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所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所侵犯的客體種類較多,其社會危害性較大,但是是否就能簡單將本罪客體理解為復雜客體呢?從復雜客體的定義來看,必須要某種犯罪行為同時直接侵犯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具體社會關系,才能說某種犯罪行為侵犯了復雜客體。而從幫助毀滅、偽造證據所直接侵犯的客體來看,其直接侵犯的客體只有正常的司法活動秩序,因而,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侵犯的客體應當是簡單客體,而非復雜客體。
二、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客觀方面
(一)“幫助”的對象“當事人”應作廣義解釋
根據我國《刑法》第307條第2款之規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對象為當事人,在此我們應當根據訴訟法的相關理論,對“當事人”的內涵采廣義的理解,該“當事人”既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活動當中的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等,也應當包括附帶民事訴訟當中的被告人及原告,且在民事、行政訴訟活動當中的原告和被告也應當納入該范疇之內,從廣義的角度對該罪名當中的“當事人”進行解釋也與立法初衷相符。
(二)“幫助”行為具體內容之“毀滅、偽造證據”
“毀滅證據”即妨礙證據出現,導致有證明力的證據無法出現在訴訟活動當中。例如,燒毀、撕爛、腐蝕證據等,使得證據形式被毀滅,也包括證據形態的喪失,如涂改等行為;“偽造證據”則是通過編制等方式導致原本沒有的證據出現或者對現有的證據予以整理、加工、篡改,導致其證明內容與爭先不符。上述行為都是行為人為了妨礙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通過使證據的證明力降低甚至消失,來避免真實證據在訴訟活動當中發揮其積極的證明力。
(三)“幫助”行為所直接作用之“證據”應作廣義解釋
對于“幫助”行為所直接作用的證據應當采廣義解釋的觀點予以理解,既包括已經被查證屬實的證據,也應當包括證據資料或者其原始素材。但是,其形式應當限定于鑒定結論、書證、已經書面化或者已經轉化為視聽資料形式的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等形式,而不應過于進行擴大解釋。
(四)“幫助”行為不僅可在訴訟活動之中,也可以在訴訟活動啟動之前
根據我國《刑法》第307條第2款之規定,被幫助的對象為“當事人”,那這是否說明,幫助行為也只能是在訴訟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實施呢?若給予上述問題肯定回答,顯然是有違司法公正的。正如前文所述,對于“當事人”的概念和內涵范疇我們應當運用訴訟法理論采廣義的看點,并不僅僅包括訴訟活動主體,所以,“幫助”行為并非以訴訟活動的開始為前提。所以,幫助行為既可以發生在訴訟活動過程之中,也同樣可以發生于訴訟活動啟動之前。
(五)“幫助”并不以被幫助人有犯罪行為為前提
“幫助”的行為是否需要以被幫助人的行為屬于犯罪行為作為其行為定性的前提?當前,理論界關于該問題產生了分歧。部分學者認為,幫助人的“幫助行為”以“被幫助人的犯罪為前提”或者“以被幫助人的違法犯罪為前提”,否則該“幫助”行為顯然也不應當構成犯罪。但是,也有部分學者持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幫助”的行為并不是以幫助人的行為屬于犯罪行為為前提,換言之,只要被幫助人的行為涉嫌犯罪,其“幫助”行為即成立。筆者更贊同后者觀點。正如前文關于訴訟時限的描述可以看出,“幫助行為”可以貫穿于訴訟活動之中,而被幫助人的行為唯有經過司法審判才能對其行為予以定性,因此,只要被幫助人的行為涉嫌犯罪,其“幫助”行為即成立。
(六)“幫助”行為須達到“情節嚴重”方可定罪
本罪屬于情節犯,唯有當事人的行為的情節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才可以適用本罪的相關規定對其追究刑事責任,換言之,若行為人具有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但是其行為尚不足以達到嚴重程度的,則不適用《刑法》對其行為追究刑事責任。
三、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主體
(一)本罪主體為自然人一般主體,單位不能成為本罪主體
根據我國刑法之規定,本罪的犯罪主體是指排除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以外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因而不難看出,單位不能成為本罪的犯罪主體,此外,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具有上述行為時適用《刑法》第306條規定的妨害作證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盡管,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5條之規定,單位作為主體由偽造證據、毀滅證據等行為的應當追究法律責任,但是我國刑法尚未就單位具有偽造證據、毀滅證據的行為進行規范,根據罪刑法定的原則,單位尚不能構成本罪的犯罪主體。
(二)當事人不能成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主體
根據德國“癖馬案”的期待可能性理論,同樣可以適用于考究當事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究竟是否觸碰刑律。當事人在實施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時,為掩蓋其犯罪事實所作出的一系列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所以,從期待可能性的理論角度來看,當事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不應當再予以刑事懲罰,當事人不能構成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罪的本罪主體。
(三)當事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不能成為本罪教唆犯
當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當中都未能針對當事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能不能成為本罪教唆犯的問題達成統一意見。以德國刑法為代表的立法例對于上述問題持肯定意見,但是,也有很多國家尚未就上述問題出臺立法予以明文立法規定,甚至在這些國家,肯定說與否定說并行。筆者認為,當事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不能成為本罪教唆犯,第一,考慮到相較于當事人自己直接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而言,其教唆他人偽造、毀滅證據的行為顯然社會危害性更輕,而若對于前者的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而對后者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顯然是自相矛盾的。第二,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是行為自己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還是教唆他人實施上述行為,由于都不具備期待可能性,所以當事人無法成為教唆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犯罪主體。
四、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之主觀方面
我國刑法中將幫助、毀滅證據的行為認定為故意犯罪,該故意不僅僅包括行為人明知其為證據而進行幫助當事人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的直接故意,也應當包括行為人明知其為證據而采取基于其他原因而實施犯罪行為并對其可能給司法活動的客觀公正性造成的影響持放任的態度的間接故意。
(一)須正確區分犯罪動機與犯罪故意
對于偽造證據罪來講,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動機在實踐中常常存在難以區分的情況。首先,犯罪動機一般不影響案件的定性,只影響對被告人的量刑。其次,我們要注意的是本罪的犯罪動機具有多樣性,除了是當事人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之外,還有其他可以成立本罪的動機。而對于行為人是否有幫助當事人逃避或減輕法律責任的希望或者其他動機,則不會影響本罪的成立;最后,從立法的角度上出發,法律要制裁這種嚴重妨礙正常法律秩序的行為。行為人這種明知其行為是在幫助犯罪嫌疑人毀滅、偽造證據,并對偵查機關的正常偵查活動造成妨礙的情況下,仍然毀滅或偽造證據,其行為會造成嚴重的危害后果,故應對其這種主觀故意、客觀危害的行為進行懲罰。
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實踐當中,不能夠片面的關注在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明知其行為是在幫助當事人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這一動機上,否則將很容易導致行為人否認這一幫助當事人逃避或減輕法律責任的動機從而不能夠使其入罪。倘若行為人是在不知道他人已經實施了犯罪行為,亦不知其行為使有關之證據被毀滅或改變,但是客觀上卻存在著妨礙司法取證的行為,對于這種行為筆者認為不應當包括在本罪之中。
(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筆者翻閱我國國內刑法學書籍以及相關著作發現,我國理論界對于本罪的主觀方面認定都是故意,但是并未對本罪的故意屬于主觀故意還是屬于間接故意做出明確界定,因此理論界在對本罪的主觀方面存在著爭論。筆者對本罪應包括間接故意持認同態度。所謂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當中,有許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案件都是以不作為的行為而體現的。例如旅館老板和清潔員工在客房內發現一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體時,即使旅館老板未對該清潔員工下達清理現場、轉移尸體的命令,而是對于清潔員工毀滅證據的行為不聞不問、不加阻止,但其作為一名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對于事物有正常的辨別能力,應當知道清理房間和轉移尸體是對刑事證據的毀壞,從而導致司法機關在案件偵破中存在困難,但其仍然對清潔員工的毀滅證據行為采取聽之任之的放任態度,以不作為的方式觸犯本罪,若在此情況下仍舊將本罪的主觀方面限于直接故意的話,就會使得這種妨礙司法秩序的行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使得犯罪分子逍遙法外,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所以,為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對犯罪分子更好的制裁,本罪的故意應當既包含行為人希望當事人逃避或減輕法律責任的直接故意,也包含行為人對毀壞、偽造證據從而妨礙司法偵查活動的間接故意。
參考文獻:
[1]鮮鐵可.妨害司法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2]陳正沓.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認定中的疑難問題探析.政治與法律.2003(4).
[3]張明楷.論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山東審判.2007(1).
[4][德]德國刑法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5]李希慧.刑法解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5.
還有70%,馬上登錄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