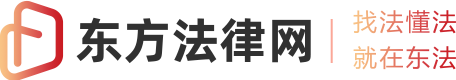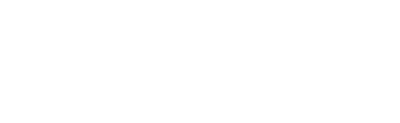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性質與界限
- 期刊名稱:《檢察實踐》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的罪名,該罪的設立為懲治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與之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正確地把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性質,合理地劃清該罪與其他犯罪之間的界限,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立足于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性質與界限進行法教義學的分析。
一、居無定所:傳銷犯罪的前史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雖然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罪名,但并不意味著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前,該種行為不受處罰。事實上,此前,我國行政法規就明文禁止傳銷活動,傳銷行為經由司法解釋得以暫時棲身于非法經營罪之中。但因為缺乏傳銷犯罪的獨立罪名,使其處于一種居無定所的狀態。可以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設立存在一個演變過程。正確地對這一立法過程進行梳理,對于我們把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性質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對于傳銷活動的禁止,始于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鑒于傳銷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負面作用,國務院發出通知明令禁止傳銷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知》第2條指出:“自本通知發布之日起,禁止任何形式的傳銷經營活動。此前已經批準登記從事傳銷經營的企業,應一律立即停止傳銷經營活動,認真做好傳銷人員的善后處理工作,自行清理債權債務,轉變為其他經營方式,至遲應于1998年10月31日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或注銷登記。逾期不辦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其營業執照。對未經批準登記擅自從事傳銷經營活動的,要立即取締,并依法嚴肅查處。”這一規定向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在《通知》發布之前,傳銷是被法律所允許的,并且從事傳銷經營的企業還經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批準登記。那么,這里的傳銷與此后被禁止的傳銷是否屬于同一個概念呢?這是令人疑惑的。上述《通知》并沒有對傳銷這個概念進行定義,因此也就無從了解法律所允許的傳銷的含義。在此,似乎混淆了這兩個概念,這就是傳銷與直銷。
傳銷與直銷是兩種不同的商品銷售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兩者往往被混同。2005年8月23日國務院頒布了《禁止傳銷條例》,同日,國務院還頒布了《直銷管理條例》:兩個條例分別代表了對傳銷的禁止和對直銷的允許的截然相反的法律立場。
根據禁止傳銷條例第2條的規定,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上述《條例》第7條還采取列舉方式規定,下列行為,屬于傳銷行為:(一)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在以上三種傳銷行為中,第一種行為屬于拉人頭,第二種行為屬于收取入門費,第三種行為屬于團隊計酬。在以上三種行為中,收取入門費的傳銷較為容易認定。而拉人頭和團隊計酬的傳銷則不太容易區分,兩者的區別在于:拉人頭是單純地以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而團隊計酬則是以發展人員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傳銷活動的特點在于發展人員,在組織者或者經營者與被發展的人員之間形成上線和下線的關系,上線從下線獲取一定的報酬。
根據直銷管理條例,直銷是指直銷企業招募直銷員,由直銷員在固定營業場所之外直接向最終消費者(以下簡稱消費者)推銷產品的經銷方式。因此,直銷的特點在于:直銷員向消費者直接銷售商品。這種銷售方式免除了中間環節,是一種無店鋪的銷售,因此具有經濟性。從層級上來說,直銷可以分為單層次直銷和多層次直銷。換言之,無論是單層次直銷和多層次直銷都屬于直銷的范疇。但根據我國直銷管理條例,單層次直銷是經批準允許存在的直銷經營模式,而多層次直銷屬于傳銷,是禁止傳銷條例明令禁止的經營行為。應該說,法律允許的直銷和法律禁止的傳銷之間還是存在明顯的區分:從計酬方式上看:直銷人員之間沒有連帶關系,依賴個人業績計酬。而傳銷人員之間具有連帶關系,實行團隊計酬。此外,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經營者要求參加者通過繳納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變相繳納入門費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的資格,并從中獲得回報。而直銷公司則不收入門費,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即可依法取得直銷員的資格。
雖然禁止傳銷條例是2005年頒布的,但如前所述,對傳銷活動的治理始于1998年,當年4月18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此后,2000年8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銀行《關于嚴厲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一》),《意見(一)》第2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下列傳銷或變相傳銷行為,要采取有力措施,堅決予以取締;對情節嚴重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機關,按照司法程序對組織者依照《刑法》225條的有關規定處理:(一)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從事無店鋪經營活動,參加者之間上線從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提取報酬的;(二)參加者通過交納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含服務,下同)等變相交納入門費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加入的資格,并以此獲取回報的;(三)先參加者從發展的下線成員所交納費用中獲取收益,且收益數額由其加入的先后順序決定的;(四)組織者的收益主要來自參加者交納的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的費用的;(五)組織者利用后參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費用支付先參加者的報酬維持運作的;(六)其他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或以高額回報為誘餌招攬人員從事變相傳銷活動的。”《意見(一)》已經明確規定,對于上述6種非法傳銷行為應當根據刑法第225條的有關規定處理,而刑法第225條是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規定。按照《意見(一)》的規定,不僅團隊計酬的經營型傳銷行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而且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的詐騙型傳銷行為也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雖然《意見(一)》只是一個經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部門規章,并不具有刑事立法效力。但在當時我國刑事法治還不健全的背景之下,《意見(一)》對于傳銷活動的定罪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傳銷活動入罪的法律根據還是司法解釋,這就是2001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批復》指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粵高法[2000]101號《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和變相傳銷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對于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發布以后,仍然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實施上述犯罪,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點:
(一)入罪的行為是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
在此,《批復》把入罪的行為表述為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從《批復》對構成要件行為的表述來看,并沒有區分傳銷的組織者或者經營者,只要參加傳銷活動的,即具備了入罪的行為要件。由此可見,打擊范圍還是較為寬泛的。當然,《批復》還是對入罪條件做了某種限制性規定,即只有情節嚴重才能構成犯罪。此外,前述《意見(一)》對傳銷行為的表述涉及變相傳銷活動。也就是說,除了典型的傳銷活動以外,還包括變相傳銷活動。那么,如何界定所謂變相傳銷活動呢?變相傳銷活動的提法來自《通知》,《通知》提出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查禁各種傳銷和變相傳銷行為。在《通知》第三條列舉的行為中,就包含了假借專賣、代理、特許加盟經營、直銷、連鎖、網絡銷售等名義進行變相傳銷的;采取會員卡、儲蓄卡、彩票、職業培訓等手段進行傳銷和變相傳銷,騙取入會費、加盟費、許可費、培訓費的;以及其他傳銷和變相傳銷的行為。因此,這里的變相傳銷是指銷售手段、入門費的稱謂等形式上的不同表現。就此而言,這種所謂變相傳銷行為還不能與典型傳銷行為相提并論。
(二)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對于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是《批復》最為重要的內容。我國刑法第225條對非法經營罪的規定,采取的是空白罪狀的立法方式。其中第4項規定的是“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是一個兜底式的規定,為《批復》的入罪解釋留下了極大的余地。因此,將刑法所沒有規定的傳銷行為解釋為非法經營行為,也就成為在不經刑事立法程序而將傳銷行為入罪的最佳選擇。
當然,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即《通知》本身并沒有對傳銷或者變相傳銷加以界定。如果對這里的傳銷承襲《意見(一)》的理解,那么,在《意見(一)》規定依照《刑法》225條的有關規定處理的6種行為中,除了第1種傳銷行為,即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從事無店鋪經營活動,參加者之間上線從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提取報酬,具有經營性質以外;其他5種傳銷行為,例如,參加者通過交納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含服務,下同)等變相交納入門費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加入的資格,并以此獲取回報的;先參加者從發展的下線成員所交納費用中獲取收益,且收益數額由其加入的先后順序決定的;組織者的收益主要來自參加者交納的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的費用的;組織者利用后參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費用支付先參加者的報酬維持運作的;其他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或以高額回報為誘餌招攬人員從事變相傳銷活動的。這些傳銷行為都沒有經營內容,實際上屬于以傳銷為名的詐騙犯罪。
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還是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行為。對于詐騙性質的傳銷則以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論處。當然,因為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因此這一界限也不明確。因此,司法實踐中存在某些定罪混亂的現象,也是在所難免的。
(三)實施傳銷行為,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
該司法解釋在《批復》的最后,還有一句話:“實施上述犯罪,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應該說,這句話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其實,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規定。這一規定表明,在實施傳銷行為的時候,可能觸犯其他罪名,對此應當從一重罪處斷。那么,在實施傳銷行為的時候,會觸犯什么罪名呢?對此,在有關傳銷的法律規定中,其實已經有蛛絲馬跡。例如,《通知》第1條在論及禁止傳銷活動的根據時,指出:“不法分子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嚴重背離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利用傳銷吸收黨政機關干部、現役軍人、全日制在校學生等參與經商,嚴重破壞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利用傳銷進行價格欺詐、騙取錢財,推銷假冒偽劣產品、走私產品,牟取暴利,偷逃稅收,嚴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在此,《通知》提及傳銷行為可能觸犯的其他罪名,包括詐騙罪、銷售偽劣產品罪、走私罪、偷稅罪(現已改為逃稅罪)等。
傳銷行為在性質上的復雜性,也為此后的立法帶來一定的爭議。在《批復》頒布以后,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從事傳銷活動的行為,一般都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在少數情況下,涉及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1}(P.482)。而兩者區分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存在實際的經營活動。
案例I朱慶文等非法經營案{2}(P.220-233)
被告人朱慶文,男,1968年2月13日出生,廣西南寧市人,漢族。
2004年9月底,朱慶文與王愛云以廣西大順公司、順昌大順公司的名義,共同策劃,制定了“周周樂IC卡”發售計劃。朱慶文先后糾集、雇傭了被告人洪少彬等人參與實施該計劃。該計劃即以消費者直接向該公司購買螺旋藻、靈芝膠囊等保健品取得會員資格,后享受每周一次的高額返還營銷款,然后以消費者所購IC卡金額、份額多少將會員分為業務員、業務主管、加盟商,業務主管與業務員之間存在上下線關系,上線可從其發展的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按不同比例提成,享受津貼。“周周樂IC卡”分為三種,即面值360元的健康卡、面值1200元的金卡和面值3000元的白金卡。高額返款即消費者每購買一份健康卡,除可提取同等價值的保健品外,每周還可獲取返還的勞務費90元,17周內最高返款累計1500元;購買一份白金卡,除可直接提取同等價值的保健品外,每周還可獲取返還的勞務費249元,20周內最高返款累計4980元。
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朱慶文等人違反國家規定,合伙進行傳銷,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繳納費用,同時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進行非法經營,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經構成非法經營罪。
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25條第(四)項、第25條第1款、第26條、第27條、第64條、第67條第1款、第7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的規定,判處被告人朱慶文有期徒刑13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00萬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分別判處2年零6個月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審判決以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
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審判決。
上述案例是刑法修正案(七)頒布之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對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一個典型案例。該案的“解說”(相當于裁判理由)在論及該案為什么定非法經營罪而不定詐騙罪或集資詐騙罪的依據時,指出:(1)該案傳銷行為存在貨物買賣行為,消費者可以用“周周樂IC卡”刷出保健產品,朱慶文在博白龍潭有螺旋藻生產基地,向綠冬公司購買保健產品。而詐騙一般沒有或者很少有貨物經營行為。(2)傳銷的利益主要依靠傳銷人自己層層發展下線來獲取,沒有下線就沒有利益。行為人陳述的周周樂IC卡推廣計劃的利潤來源,主要是建立在購卡者能在消費完原面額后仍繼續充值消費的基礎上產生,但這種假設是不現實的。詐騙則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承諾以定期利息、紅利等形式返還巨額利益相引誘。(3)報表、審計報告、賬戶清單和行為人供述、證人的證言可證實,行為人已經返還業務員大約幾千萬余元的本金及勞務費,可見確有返還大量勞務費,而詐騙返還的款項一般較小。以上對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傳銷行為與詐騙性犯罪的區分的論述,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當時《通知》所規范的是指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行為。這個意義上的傳銷行為,是一種法律所禁止的經營行為。在上述“解說”中,就明確地把傳銷界定為是一種未獲批準直銷經營許可的行為,指出:“傳銷,在國外又稱直銷,即指用傳遞方式進行銷售,一般是指企業不通過店鋪經營等流通環節,將產品或服務直接銷售、提供給消費者的一種營銷方式。”在此,“解說”把傳銷視為是直銷的營銷方式,朱慶文的大順公司所實施的傳銷行為之所以構成非法經營罪,是因為未獲得直銷經營許可。這一對傳銷行為的理解,把它與以傳銷為名所實施的各種詐騙犯罪加以區分。
然而,上述對傳銷的界定不僅與《意見(一)》關于傳銷的界定不同,而且與禁止傳銷條例關于傳銷的概念也不一致。禁止傳銷條例第7條所列舉的3種傳銷行為中,所謂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實則并無經營內容,只有團隊計酬具有經營內容。當然,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拉人頭、收取入門費與團隊計酬競合的情形。
二、經營型傳銷抑或詐騙型傳銷:立法過程的逆轉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七)單獨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罪名之前,根據司法實踐的規定,對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行為(區別于以傳銷為名實施的詐騙犯罪)是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由此而解法律根據缺乏的一時之需。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司法實踐要求對傳銷行為專門設立罪名。我國學者指出:僅僅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傳銷和變相傳銷的性質加以規定,將傳銷行為納入非法經營罪的范疇,很難適應傳銷和變相傳銷的新特點,必須獨設非法傳銷罪,明確設定非法傳銷的刑罰{3}。對傳銷犯罪進行立法的建議得到立法機關的回應,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得以完成。
在刑法修正案(七)的制定過程中,對于傳銷犯罪如何設立罪名,存在爭議,并且前后發生了重大的變更。在2008年8月25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稿第4條中,對于傳銷犯罪是這樣規定的:在刑法第225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25條之一:“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犯罪行為的組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傳銷犯罪行為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這一規定是將傳銷犯罪的組織行為規定為犯罪,因此是一種組織罪。我國刑法中的組織行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共犯的組織行為,另一種是規定為正犯的組織行為。前者根據刑法總則的規定,以共犯論處,而并沒有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后者根據刑法分則的規定,以單獨犯罪論處。例如我國刑法第120條規定的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以及第294條規定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而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稿對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罪的規定,就屬于以單獨犯罪論處的組織罪。值得注意的是,該草案還規定:“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這就是說,對于具體實施傳銷犯罪活動的,還是按照非法經營罪、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顯然也是參照刑法第120條和第294條第2款的規定。如此,則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的行為構成一個組織犯罪。如果該傳銷組織又從事傳銷活動的,則根據傳銷的性質又分別定罪:傳銷而具有經營內容的,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傳銷而具有詐騙或者集資詐騙性質的,以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論處,并實行數罪并罰。
立法機關在論及這一規定的背景時,指出:“國務院法制辦、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提出,當前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方式組織傳銷的違法犯罪活動,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危害嚴重。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這類案件主要是根據實施傳銷行為的不同情況,分別按照非法經營罪、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為更有利打擊組織傳銷的犯罪。應當在刑法中對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組織的犯罪作出專門規定。經同有關部門研究,建議在刑法中增加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的犯罪。對實施這類犯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實行數罪并罰”。[1]因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上述規定是在原有司法解釋將傳銷行為納入非法經營罪規定的基礎上,對組織、領導傳銷組織行為的特別規定。
那么,這里傳銷組織的傳銷一詞如何理解呢?換言之,這里的傳銷是指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還是指以傳銷為名的詐騙?對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雖然并不明確,但草案有“傳銷犯罪行為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專款規定,這里的行政法規包括前述《禁止傳銷條例》,而《禁止傳銷條例》明確把詐騙型傳銷和經營型傳銷都納入傳銷的范圍,因此,這是一種較為寬泛的傳銷概念。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上述規定,在法案審議中提出了一些意見,主要認為該罪的規定過于籠統,尤其是對傳銷行為按照行政法規確定,使該罪的構成要件呈現為空白狀態,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為此,2008年12月25日草案第2稿第4條中,對該罪的規定做了修改:在刑法第224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刑法修正案(七)最后定稿也采納了這一規定。從定稿的規定來看,不僅對傳銷活動進行了界定,更為重要的是將組織罪修改為詐騙性質的傳銷犯罪。并且,該條也從刑法第225條之一變更為刑法第224條之一。而刑法第224條是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從而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性質確定為詐騙犯罪。
如前所述,根據《禁止傳銷條例》7條對傳銷的列舉式規定,存在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和團隊計酬這三種傳銷方式。但在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關于傳銷的概念中,只規定了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的傳銷形式,恰恰沒有規定具有經營內容的團隊計酬的傳銷形式。至此,刑法修正案(七)關于傳銷犯罪的規定,在性質上發生了逆轉:從經營型傳銷改變為詐騙型傳銷。傳銷這個概念在我國刑法中的界定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傳銷本來是一種經營方式,就此而被我國刑法確定為一種詐騙方式。
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法教義學的考察
經過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正,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后,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頒布了《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二)》),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做了專門規定。對于上述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在理解與適用中存在以下需要研究的問題:
(一)罪名的推敲
在刑法修正案(七)通過以后,200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將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規定的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罪名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無疑,組織、領導是本罪的重要行為方式,但這一罪名概括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說是以偏概全。因為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表述句式是:組織、領導……,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在這一表述中,騙取財物雖然被包裹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這一句式之中,但它卻是對于本罪具有決定性的用語。在這種情況下,較為合理的罪名應該是傳銷詐騙罪。因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只是詐騙手段,其行為本身還是詐騙。
我們可以將刑法第224條之一與刑法第224條的規定相比,第224條是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在這一規定中,立法機關也列舉了5種合同詐騙行為。但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并沒有以這5種行為確定罪名,而是以這5種行為的共同屬性——合同詐騙確定罪名。如果說,5種行為難以概括,因此不能以此為罪名。那么,我們比較刑法第194條第2款的規定:“使用偽造、變造的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他銀行結算憑證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對此,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并沒有根據罪狀,將罪名概括為使用偽造、變造的金融憑證罪,而是將罪名確定為金融憑證詐騙罪。因為使用偽造、變造的金融憑證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詐騙的特殊表現形態。刑法第224條之一也是如此,雖然條文主體內容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但基于該條文對于傳銷的內容界定,組織、領導這種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為主要特征的傳銷活動,其實就是一種詐騙的特殊類型。因此,以傳銷詐騙罪概括本罪的罪名,是最為確切的。在目前將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罪名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情況下,由于在罪名中沒有突出詐騙的性質,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傳銷并不必然是詐騙,因此傳銷詐騙一語似乎存在問題。但這里的傳銷詐騙是以傳銷為名所實施的詐騙,正如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詐騙一詞,合同與詐騙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里的合同詐騙,只不是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所實施的詐騙一語的簡稱而已。
(二)罪體的界定
根據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客觀上表現為組織、領導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為特征的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行為。
1.組織、領導
在刑法修正案(七)頒布之前的司法解釋中,將傳銷犯罪的行為表述為從事傳銷活動。這里的從事,是指實施。因此,對傳銷犯罪的行為界定得極為寬泛。刑法第224條之一則將行為表述為組織、領導,由此表明只有組織者和領導者的行為才構成犯罪,而一般傳銷活動的參與者則不構成犯罪。這一對行為的限縮,具有刑事政策的重大蘊含,體現了縮小打擊面的政策思想。既然是傳銷詐騙罪,那么,為什么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員不構成本罪呢?對于一般的詐騙罪而言,只要參與詐騙活動的,無論是主犯還是從犯,都構成犯罪。但傳銷詐騙與之不同,只有這些傳銷詐騙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才是詐騙行為的實施者,而一般的參與者具有被引誘或者被脅迫的性質。雖然有些人也從傳銷中非法獲利,但從整體上說,這些參與者還是屬于被害人。正如在集資詐騙罪中,只有那些集資詐騙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構成犯罪,而一般的參與集資的人員,則屬于被害人。
根據前引《意見(二)》的規定,下列人員可以認定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的人員;在傳銷活動中承擔管理、協調等職責的人員;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曾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刑事處罰,或者1年以內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又直接或者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15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人員;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上述規定,雖然是以對組織者、領導者的列舉式規定的形式出現的,但其中包含了對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行為的描述。根據上述《意見(二)》的規定,傳銷活動中的組織行為是指傳銷活動中的發起、策劃、操縱行為;而領導行為是指傳銷活動中的管理、協調行為;以及傳銷活動中的宣傳、培訓行為等。
2.傳銷活動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前,當時在法律上對于傳銷的理解是存在混亂的。主要問題在于:法律上的傳銷是指經營型的傳銷還是指詐騙型的傳銷?顯然,在對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法律語境中,這里的傳銷只能是經營型的傳銷而非詐騙型的傳銷,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罪狀中,立法機關已經對傳銷做了定義式的規定。按照該規定,傳銷包括兩種情形: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這就是所謂拉人頭;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這就是所謂收取入門費。在這兩種傳銷活動中,都沒有經營的內容,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銷。而是以傳銷為名,實際上是一種詐騙行為。
3.騙取財物
騙取財物是組織、領導傳銷罪的本質特征,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具有重要意義。關于騙取財物的行為,我國學者指出:“所謂騙取財物,是說由于傳銷行為屬于非法,所以通過傳銷活動取得的返利、報酬等任何財產,均屬于騙取財物。至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實際上是否騙取到了財物,不影響本罪的構成。也就是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不以騙取財物為必要。所以,‘騙取財物’屬于本罪可有可無的概念。”{4}(P.378)以上對于騙取財物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中的地位與意義的說法,我是不能茍同的。
首先,不是因為傳銷活動非法,所以通過傳銷活動取得的財產才屬于騙取的財物。而是因為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方法進行傳銷活動,其本身就屬于詐騙,因而其所取得的財物才是騙取的財物。
其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當然以騙取財物為其構成犯罪的要件。如果沒有騙取財物的,就不能構成本罪。當然,考慮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特殊性,本罪不以騙取的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是以發展傳銷人員的人數和層級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但這并不意味著騙取財物的數額對于本罪的定罪不重要。
再次,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來說,騙取財物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概念,而是不可或缺的內容。《意見(二)》對此也做了明文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參與傳銷活動人員是否認為被騙,不影響騙取財物的認定。”而且,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性質,也是詐騙型傳銷與經營型傳銷的根本區分之所在。
在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法第224條之一中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詐騙財物與詐騙之間的關系,存在非同一性說的見解。這種觀點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騙取財物與詐騙不是同一性質的行為。例如,我國學者指出:
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的規定中,雖然有“騙取財物”的特征表述,但傳銷活動“騙取”的含義,卻是推銷質差、價低等,冒充高質、高價位的“道具商品”或者“服務”,通過發展下線購買的人頭多少而獲取相應的高額回報。也就是說,傳銷不是以直銷產品或者實質性服務作為銷售者、推介者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而是以“拉人頭”的方式,賺取“人頭費”或高額“入會費”作為傳銷者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但這里的傳銷的道具商品仍然是商品,服務仍然是服務,只是不是其所描述的商品、服務而已,這是與詐騙非同一性質的行為。{5}(P.472)
這種觀點試圖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與詐騙加以區分,認為兩者并非同一種行為。筆者認為,這一理解是不妥的。以傳銷為手段的詐騙具有其特殊性,例如采取了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方法,以此騙取財物,這是不可否認的。但以此特殊性而否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與詐騙具有同一性,這也是不可取的。
此外,張明楷教授則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騙取財物是對詐騙型傳銷組織(或者活動)的描述,亦即,只有當行為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具有“騙取財物”的性質時,才成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為顯示詐騙型傳銷組織(或活動)特征的“騙取財物”,不以客觀上已經騙取了他人財物為前提{6}(P.748)。這種觀點肯定采取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的手段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行為本身具有詐騙財物的性質,即承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詐騙財物與詐騙之間存在同一性,這是正確的。但這種觀點又考慮到刑法第224條之一所采取的“組織、領導拉人頭、收取入門費,騙取財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傳銷活動”這一表述,認為本罪的行為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并不是獨立的行為,只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這一行為的性質。筆者認為,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稿第4條將本罪的行為表述為“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犯罪行為的組織”,這是一種組織罪的立法表達。及至草案第2稿第4條修改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時候,仍然沿襲了先前的表述,沒有相應地改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而確定為“組織、領導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作為形式,騙取財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傳銷活動”的罪狀。在此,騙取財物不是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相并列的行為要素,而是用來界定傳銷活動的形容用語。盡管如此,筆者認為還是要把本罪的構成要件概括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因此,騙取財物并不僅僅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行為的性質,而且是本罪獨立的客觀要素。因為詐騙犯罪在構成要件上具有其特殊性,不僅要有被告人的欺騙行為,而且包含了被害人因欺騙而產生認識錯誤,基于這種認識錯誤而交付財物的行為,這才是對詐騙型傳銷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完整表述。
在此涉及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詐騙罪和集資詐騙罪之間的關系。對此,張明楷教授一方面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具有詐騙的性質;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認為刑法第224條之一與規定集資詐騙罪的第192條、規定普通詐騙罪的第266條是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關系,進而對以傳銷方式實施詐騙的案件適用特別法條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7}張明楷教授是以如果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對詐騙型傳銷只能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為理由,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詐騙罪和集資詐騙罪之間不是法條競合關系,而是想象競合關系,以便實行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但筆者認為,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在本體上存在區分,不能因為不同犯罪的法定刑輕重設置而混淆兩者之間的界限。更不贊同模糊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之間的界限的觀點{8}。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為傳銷詐騙罪,其與詐騙罪之間顯然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的競合關系。對此,只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盡管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高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至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的關系,則稍顯復雜。因為相對于詐騙罪而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都屬于特別法。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而言,不能認為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的法條競合關系,但可以認為存在交互競合關系。對此,可以按照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處理。
(三)罪責的界定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罪過形式是故意,這是沒有問題的。存在爭議的問題在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如何理解。對此,我國刑法學界存在非法牟利目的說與非法占有目的說之分。非法牟利目的說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是以牟利為目的。例如,我國學者指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為人明知自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為法律所禁止,但卻通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達到騙取錢財,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1}(P.482)非法占有目的說則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例如我國學者指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并且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9}(P.686)”這里的騙取財物的目的完全可以理解為非法占有的目的。當然,這里沒有明確地采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提法,也還是反映出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某種猶豫和踟躕態度。
在以上兩種觀點中,非法牟利說是通說。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牟利目的與營利目的并無區分。在大多數罪狀中,立法者都采用了以營利為目的的表述,只有個別犯罪稱以牟利為目的。無論是以營利為目的還是以牟利為目的,其前提是存在經營行為。因此,這種把以牟利為目的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的觀點,與對本罪的傳銷行為是否具有經營性的理解存在直接的關聯性。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本罪之前,對于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傳銷犯罪,將其主觀違法要素確定為以牟利為目的或者以營利為目的,都是正確的。但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傳銷活動是詐騙型傳銷的情況下,仍然承襲以牟利為目的的表述,就存在問題。筆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屬于傳銷詐騙罪,是詐騙罪的特殊法。因此,對于本罪的主觀違法要素,應該表述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四)罪量的界定
刑法第224條之一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沒有規定罪量要素,但并非只要實施了這種傳銷詐騙行為,就一概構成犯罪。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二)》(以下簡稱《追訴標準》)第78條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根據這一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只有達到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規模,才能構成本罪。
案例II程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10}(P.61-63)
2012年5月底至6月初,被告人程某在博愛縣打著“山東陽光電子商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陽光公司)”的旗號,在被告人郝某的幫助下,在博愛縣清化鎮重陽路以其妻子王愛利的名義設立報單中心,推銷該公司無任何使用價值的電子幣,以繳納一定費用購買電子幣獲得加入資格,成為陽光公司的會員,并按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和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進行傳銷活動。
該傳銷活動經營模式為:每單1000元對應購買陽光公司1000電子幣,每人最多購買8單,獲得加入資格成為會員,每天按營銷計劃獲得返利。會員每發展1名人員加入,可獲得獎勵100元。成為繳納2000元購買2000電子幣可單獨設立報單中心,設立報單中心后,每向陽光公司報1單業務可獲得報單費30元。
截至案發,程某共計直接或間接發展人員96人且層級達9級,涉案金額481000元。被告人程某非法所得14400元,被告人郝某非法所得9620元。案發后,被告人程某退交非法所得4980元。
對于本案,博愛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程某、郝某組織、領導以推銷電子幣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購買電子幣的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且直接或者間接發展人員96人層級達9級,其行為均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告人程某、郝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
博愛縣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1條之一、第67條第3款、第64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一、被告人程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
二、被告人郝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
三、對被告人程某退交的非法所得4980元,予以沒收。對被告人程某非法所得的9420元,被告人郝某非法所得的9620元,予以追繳。
對于本案的定性,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程某、郝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并使他人陷入認識錯誤,因他人基于認識錯誤而自愿處分財產,行為人獲取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所以程某、郝某構成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陳某、郝某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其行為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應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以上兩種意見顯然是按照詐騙罪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不同構成要件分別對本案事實進行了描述:詐騙罪的意見是按照行為的本質進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形成了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認識錯誤,因他人基于認識錯誤而自愿處分財產,行為人獲取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這樣一幅詐騙罪的犯罪圖景。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意見則是按照行為的表面運作進行寫真式的敘述,形成了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匯總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這樣一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犯罪輪廓。其實,以上兩種理論敘述是對同一種行為的不同角度的表達,兩者之間存在表象與本質之間的表里關系。因此,詐騙罪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客觀上是競合的。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究竟如何界定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間的關系,以便正確地對兩罪加以區分呢?對此,該案的“法官后語”指出:
出現以上兩種意見,其主要原因在于對騙取財物的不同理解。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區分的關鍵點在于主觀方面:詐騙罪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行為人主觀上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是具有非法牟利的動機。在傳銷活動中,為了不斷發展人員加入,行為人通常用高額利潤做誘餌,夸大或虛構傭金或獎金收入,收取高額入門費或強制購買產品,這似乎具有某些詐騙罪的特征,但傳銷中參加者是為追逐高額回報而加入其中,其決定交易是受到利益誘惑,而不是因虛構事實、行為誤導而導致產生錯誤認識,故其行為不是受害人行為,不受法律保護。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組織者和領導者才構成本罪,一般參加者不構成犯罪{10}(P.63)。
對于程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博愛縣人民法院的定性是完全正確的。但“法官后語”對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間關系的論述則難以成立。
這里主要還是涉及對本罪的主觀違法要素的理解:到底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還是與非法牟利為目的?本案法官否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主張以牟利為目的。正如前文所言,非法占有目的和非法牟利目的的根本區分在于:客觀上是否具有營利行為。如果是營利型的傳銷行為,主觀上當然具有營利目的。反之,如果說詐騙型的傳銷行為,則主觀上不可能具有營利目的。基于詐騙行為,主觀上只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程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已經認定被告人是以推銷電子幣的經營活動為名,采用傳銷方式,騙取他人財物。在這種情況下,主觀上怎么可能具有牟利目的而不是占有目的呢?
(五)團隊計酬的定性
團隊計酬是傳銷的一種方式,被稱為經營型的傳銷行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傳銷活動的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
關于團隊計酬到底是直銷還是傳銷的問題,在我國法律上始終是存在模糊的。在刑法修正案(七)頒布之前,無論是在《意見(一)》還是在《禁止傳銷條例》中,都是將團隊計酬納入傳銷的范疇。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則將這種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但刑法理論上,也有些學者將團隊計酬歸入直銷的范疇,認為這是直銷活動中的多層次計酬。我國學者在論及拉人頭和團隊計酬的區分時,指出:
雖然二者都采用多層次計酬的方式,但是仍有很大不同:一是從是否繳納入門費上看,多層次計酬的銷售人員在獲取從業資格時沒有被要求繳納高額入門費,而拉人頭傳銷不繳納高額入門費,或者購買與高額入門費等價的“道具商品”是根本得不到入門資格的;二是從經營對象上看,多層次計酬是以銷售產品為導向,商品定價基本合理,而且還有退貨保障。而拉人頭傳銷根本沒有產品銷售,或者只是以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的“道具商品”為幌子,且不許退貨,主要是以發展“下線”人數為主要目的;三是從人員的收入來源上,多層次計酬主要根據從業人員的銷售業績和獎金,而拉人頭傳銷主要取決于發展的“下線”人數多少和新入會成員的高額入門費;四是從組織存在和維系的條件看,多層次計酬直銷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取決于產品銷售業績和利潤。而拉人頭騙取傳銷組織則直接取決于是否有新成員以一定倍率不斷加入{11}。
依筆者之見,團隊計酬仍然屬于傳銷而非直銷。至于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則根本不是傳銷,而是以傳銷為名所實施的詐騙行為。因此,如果把團隊計酬從傳銷中抽離,傳銷這個概念就不復存在了。更何況,直銷是法律所允許的,而團隊計酬式的傳銷則為法律所禁止。
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將傳銷界定為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以后,團隊計酬的傳銷形式沒有包含在本罪的構成要件之中。對此,我國學者一般都認為,對于這種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仍然應當以非法經營罪論處。例如,張明楷教授指出:“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由于組織、領導原始型傳銷活動的行為,并不具備刑法第224條之一所要求的‘騙取財物’的要素,不能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又由于這種經營行為被法律所禁止,并且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依然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7}應該說,這一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事實上,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前,司法實踐中對這種經營型的傳銷行為本來就是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在刑法修正案(七)未對這種經營型的傳銷行為進行規定的情況下,為懲治這種傳銷行為,對其按照非法經營罪論處是完全正確的。然而,2013年11月14日《意見(二)》對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的定性問題做了以下規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與此同時還規定:“形式上采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于‘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241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將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做了非犯罪化的處理。可以說,這是對傳銷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重大調整。以下將討論的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就十分真實地反映了在司法實踐中,這種刑事政策的調整對具體案件處理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當事人命運的逆轉。
案例III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12}(P.63-68)
被告人曾國堅,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漢族,無業。2010年1月15日因本案被逮捕。
(其他被告人略)
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犯非法經營罪,向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9年6月始,被告人曾國堅租賃深圳市羅湖區怡泰大廈A座3205房為臨時經營場所,以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發展經銷商的名義發展下線,以高額回饋為誘餌,向他人推廣傳銷產品、宣講傳銷獎金制度。同時,曾國堅組織策劃傳銷,誘騙他人加入,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入會費用,取得加入和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并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以下線的發展成員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均在上述場所參加傳銷培訓,并積極發展下線,代理下線或者將下線直接帶到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繳費入會,進行交易,形成傳銷網絡:其中曾國堅發展的下線人員有鄭某妮、楊某湘、王某軍、楊某芳、袁某霞等人,楊某芳向曾國堅的上線曾某茹交納人民幣(以下未標明的幣種均為人民幣)20000元,袁某霞先后向曾國堅、曾某茹及曾國堅的哥哥曾某建共交納62000元;黃水娣發展羅玲曉、莫紅珍和龔某玲為下線,羅玲曉、莫紅珍及龔某玲分別向其購買了港幣5000元的產品;羅玲曉發展黃某梅為下線,黃某梅發展王某華為下線,黃某梅、王某華分別向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交納入會費港幣67648元;莫紅珍發展龍某玉為下線,龍某玉發展鐘某仙為下線,鐘某仙發展周某花為下線,其中龍某玉向莫紅珍購買了港幣5000元的產品,鐘某仙、周某花分別向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交納人會費港幣67648元。2009年12月8日,接群眾舉報,公安機關聯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羅湖分局將正在羅湖區怡泰大廈A座3205房活動的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等人查獲。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均構成非法經營罪,且屬于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曾國堅積極實施犯罪,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均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且犯罪情節輕微,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依法均可以免除處罰。曾國堅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對其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5條、第25條第1款、第26條、第27條、第72條之規定,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曾國堅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并處罰金1000元;以非法經營罪分別判處被告人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免予刑事處罰。
宣判后,被告人曾國堅不服,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并基于以下理由請求改判無罪:亮碧思(香港)有限公司有真實的商品經營活動,其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也沒有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曾國堅與原審被告人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行為,而不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鑒于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的行為已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故其行為不應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曾國堅的上訴理由成立。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25條第1款第(二)之規定,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撤銷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2011)深羅法刑一重字第1號刑事判決;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無罪。
上述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從法院認定的傳銷事實來看,屬于團隊計酬的形式。因此,公訴機關對于本案是以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的。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對于本案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之后,對傳銷活動的刑法評價應當實行單軌制,即僅以是否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特征進行評價,如果不符合該罪構成特征,就應當宣告無罪,而不能再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則主張雙軌制,認為刑法修正案(七)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并未明確取消非法經營罪的適用,對于傳銷活動,即使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特征,也仍然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在以上兩種意見中,法院最終采納了一種意見,宣告被告人無罪。在以上爭論中,提及所謂單軌制和雙軌制的概念。單軌制是指對于傳銷行為只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處理,這也就暗含了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團隊計酬不構成犯罪的意思。而雙軌制則認為,對傳銷行為如果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應以該罪論處。不符合該罪特征的團隊計酬傳銷行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因此,這是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設立以后,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究竟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所存在的爭議。
顯然,對于本案作出無罪判決是完全正確的。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本案提出的法律適用問題并不是“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設立以后,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究竟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而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尚未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立案追訴標準,但經營數額或者違法所得數額達到非法經營罪立案追訴標準的,能否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在這一敘述中,就隱含著本案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的傳銷行為,如果發展人數和層級達到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立案追訴標準,是可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的意思。因此,這里存在著對法律適用問題提煉上的偏差。
在本案裁判理由中,作者論述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包括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團隊計酬按照有關司法實踐不再以犯罪論處,指出:
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條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客觀行為中未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活動,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傳銷活動如何定性,存在一定爭議。鑒于此種情況,意見(二)對“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進行了專門規定。《意見(二)》第五條第一款對“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的概念進行了明確。該款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傳銷活動的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意見(二)》第五條第二款對“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的定性進行了規定。該款規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形式上采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于‘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12}(P.67-68)。
顯然,這段話并不是在審理本案當時的意見。因為當時對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不以犯罪論處的司法解釋還沒有頒布。試想,如果當時司法解釋已經頒布,對此還會存在爭議嗎?
與此同時,裁判理由又認定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的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指出:“在本案中,曾國堅等人實施了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傳銷行為。客觀上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特征。只是依照《追訴標準》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起點為‘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而現有證據顯示本案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不足三十人。”{12}(P.67)因此,本案只是沒有達到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而已。如果已經達到追訴標準,是完全可以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
顯然,本案裁判理由的上述兩個方面的論述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案件材料反映,在一審階段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曾建議羅湖區人民檢察院就傳銷人員的人數和層級進行補充偵查。羅湖區人民檢察院復函認為刑法修正案(七)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了規定,但未取消非法經營罪的適用,根據刑法第225條第四項及《批復》的規定,曾國堅等人的行為即使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也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特征,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沒有補充偵查必要。因此,即使是檢察機關也認為,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不是是否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的問題,而是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后,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還是否可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問題。
之所以出現以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情況,事實上是該案的敘述省略了時間維度有關。因為從該案材料中,我們看不到具體的審理時間。只是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的本案的案號中可以確定這是2011年受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批復是2012年。而規定團隊計酬不以犯罪論處的司法解釋是2013年11月14日頒布的。在這一司法解釋頒布之前,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是否以非法經營罪論處,法律界限并不明確,而且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對本案以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就是十分正常的。而一審判決對被告人曾國堅等人也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作出了有罪判決。第一次上訴以后,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發回重審。重一審判決仍然認定被告人曾國堅等人構成非法經營罪。再次上訴以后,對于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逐級層報請示,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刑他字第56號批復明確:“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如未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行為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亦不宜再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據此,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不足30人,亦沒有相應證據證明該傳銷體系的層級在三級以上,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改判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無罪。
在筆者看來,曾國堅案真實地反映了在關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不以犯罪論處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案件如何處理問題上的一定程度的混亂。只是在司法解釋正式出臺以后,對于這個問題的法律界限才得以明確。但問題在于,刑法修正案(七)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法,本來是要加強對傳銷活動的懲治。但立法過程的一波三折,司法解釋的限縮性規定,刑法對于傳銷活動的打擊力度不是加強而是弱化了。
這是立法者所愿意看到的嗎?不得而知。
(責任編輯 于賀清)
【注釋】 作者簡介:陳興良,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興發巖梅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1]李適時: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說明。
【參考文獻】 {1}周道鸞、張軍主編:《刑法罪名精釋》(第4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2}國家法官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編:《中國審判案例要覽》(2008年刑事審判案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熊英:“對設立非法傳銷罪的立法思考”,載《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4}曲新久:《刑法學》(第2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5}馬克昌主編:《百罪通論》(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6}張明楷:《刑法學》(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7}張明楷:“傳銷犯罪的基本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9期。
{8}張明楷:“犯罪之間的界限與競合”,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
{9}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第5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10}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5年度案例(刑法分則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11}黃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讀”,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6期。
{1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編:《刑事審判參考》第92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一、居無定所:傳銷犯罪的前史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雖然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罪名,但并不意味著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前,該種行為不受處罰。事實上,此前,我國行政法規就明文禁止傳銷活動,傳銷行為經由司法解釋得以暫時棲身于非法經營罪之中。但因為缺乏傳銷犯罪的獨立罪名,使其處于一種居無定所的狀態。可以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設立存在一個演變過程。正確地對這一立法過程進行梳理,對于我們把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性質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對于傳銷活動的禁止,始于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鑒于傳銷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負面作用,國務院發出通知明令禁止傳銷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知》第2條指出:“自本通知發布之日起,禁止任何形式的傳銷經營活動。此前已經批準登記從事傳銷經營的企業,應一律立即停止傳銷經營活動,認真做好傳銷人員的善后處理工作,自行清理債權債務,轉變為其他經營方式,至遲應于1998年10月31日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或注銷登記。逾期不辦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其營業執照。對未經批準登記擅自從事傳銷經營活動的,要立即取締,并依法嚴肅查處。”這一規定向我們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在《通知》發布之前,傳銷是被法律所允許的,并且從事傳銷經營的企業還經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批準登記。那么,這里的傳銷與此后被禁止的傳銷是否屬于同一個概念呢?這是令人疑惑的。上述《通知》并沒有對傳銷這個概念進行定義,因此也就無從了解法律所允許的傳銷的含義。在此,似乎混淆了這兩個概念,這就是傳銷與直銷。
傳銷與直銷是兩種不同的商品銷售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兩者往往被混同。2005年8月23日國務院頒布了《禁止傳銷條例》,同日,國務院還頒布了《直銷管理條例》:兩個條例分別代表了對傳銷的禁止和對直銷的允許的截然相反的法律立場。
根據禁止傳銷條例第2條的規定,傳銷是指組織者或者經營者發展人員,通過對被發展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或者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或者要求被發展人員以交納一定費用為條件取得加入資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擾亂經濟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的行為。上述《條例》第7條還采取列舉方式規定,下列行為,屬于傳銷行為:(一)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在以上三種傳銷行為中,第一種行為屬于拉人頭,第二種行為屬于收取入門費,第三種行為屬于團隊計酬。在以上三種行為中,收取入門費的傳銷較為容易認定。而拉人頭和團隊計酬的傳銷則不太容易區分,兩者的區別在于:拉人頭是單純地以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而團隊計酬則是以發展人員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傳銷活動的特點在于發展人員,在組織者或者經營者與被發展的人員之間形成上線和下線的關系,上線從下線獲取一定的報酬。
根據直銷管理條例,直銷是指直銷企業招募直銷員,由直銷員在固定營業場所之外直接向最終消費者(以下簡稱消費者)推銷產品的經銷方式。因此,直銷的特點在于:直銷員向消費者直接銷售商品。這種銷售方式免除了中間環節,是一種無店鋪的銷售,因此具有經濟性。從層級上來說,直銷可以分為單層次直銷和多層次直銷。換言之,無論是單層次直銷和多層次直銷都屬于直銷的范疇。但根據我國直銷管理條例,單層次直銷是經批準允許存在的直銷經營模式,而多層次直銷屬于傳銷,是禁止傳銷條例明令禁止的經營行為。應該說,法律允許的直銷和法律禁止的傳銷之間還是存在明顯的區分:從計酬方式上看:直銷人員之間沒有連帶關系,依賴個人業績計酬。而傳銷人員之間具有連帶關系,實行團隊計酬。此外,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經營者要求參加者通過繳納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變相繳納入門費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的資格,并從中獲得回報。而直銷公司則不收入門費,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即可依法取得直銷員的資格。
雖然禁止傳銷條例是2005年頒布的,但如前所述,對傳銷活動的治理始于1998年,當年4月18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此后,2000年8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銀行《關于嚴厲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一》),《意見(一)》第2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下列傳銷或變相傳銷行為,要采取有力措施,堅決予以取締;對情節嚴重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機關,按照司法程序對組織者依照《刑法》225條的有關規定處理:(一)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從事無店鋪經營活動,參加者之間上線從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提取報酬的;(二)參加者通過交納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含服務,下同)等變相交納入門費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加入的資格,并以此獲取回報的;(三)先參加者從發展的下線成員所交納費用中獲取收益,且收益數額由其加入的先后順序決定的;(四)組織者的收益主要來自參加者交納的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的費用的;(五)組織者利用后參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費用支付先參加者的報酬維持運作的;(六)其他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或以高額回報為誘餌招攬人員從事變相傳銷活動的。”《意見(一)》已經明確規定,對于上述6種非法傳銷行為應當根據刑法第225條的有關規定處理,而刑法第225條是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規定。按照《意見(一)》的規定,不僅團隊計酬的經營型傳銷行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而且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的詐騙型傳銷行為也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雖然《意見(一)》只是一個經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部門規章,并不具有刑事立法效力。但在當時我國刑事法治還不健全的背景之下,《意見(一)》對于傳銷活動的定罪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傳銷活動入罪的法律根據還是司法解釋,這就是2001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批復》指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粵高法[2000]101號《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和變相傳銷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對于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發布以后,仍然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實施上述犯罪,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點:
(一)入罪的行為是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
在此,《批復》把入罪的行為表述為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從《批復》對構成要件行為的表述來看,并沒有區分傳銷的組織者或者經營者,只要參加傳銷活動的,即具備了入罪的行為要件。由此可見,打擊范圍還是較為寬泛的。當然,《批復》還是對入罪條件做了某種限制性規定,即只有情節嚴重才能構成犯罪。此外,前述《意見(一)》對傳銷行為的表述涉及變相傳銷活動。也就是說,除了典型的傳銷活動以外,還包括變相傳銷活動。那么,如何界定所謂變相傳銷活動呢?變相傳銷活動的提法來自《通知》,《通知》提出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查禁各種傳銷和變相傳銷行為。在《通知》第三條列舉的行為中,就包含了假借專賣、代理、特許加盟經營、直銷、連鎖、網絡銷售等名義進行變相傳銷的;采取會員卡、儲蓄卡、彩票、職業培訓等手段進行傳銷和變相傳銷,騙取入會費、加盟費、許可費、培訓費的;以及其他傳銷和變相傳銷的行為。因此,這里的變相傳銷是指銷售手段、入門費的稱謂等形式上的不同表現。就此而言,這種所謂變相傳銷行為還不能與典型傳銷行為相提并論。
(二)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對于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是《批復》最為重要的內容。我國刑法第225條對非法經營罪的規定,采取的是空白罪狀的立法方式。其中第4項規定的是“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是一個兜底式的規定,為《批復》的入罪解釋留下了極大的余地。因此,將刑法所沒有規定的傳銷行為解釋為非法經營行為,也就成為在不經刑事立法程序而將傳銷行為入罪的最佳選擇。
當然,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即《通知》本身并沒有對傳銷或者變相傳銷加以界定。如果對這里的傳銷承襲《意見(一)》的理解,那么,在《意見(一)》規定依照《刑法》225條的有關規定處理的6種行為中,除了第1種傳銷行為,即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從事無店鋪經營活動,參加者之間上線從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提取報酬,具有經營性質以外;其他5種傳銷行為,例如,參加者通過交納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含服務,下同)等變相交納入門費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紹或發展他人加入的資格,并以此獲取回報的;先參加者從發展的下線成員所交納費用中獲取收益,且收益數額由其加入的先后順序決定的;組織者的收益主要來自參加者交納的入門費或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的費用的;組織者利用后參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費用支付先參加者的報酬維持運作的;其他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絡或以高額回報為誘餌招攬人員從事變相傳銷活動的。這些傳銷行為都沒有經營內容,實際上屬于以傳銷為名的詐騙犯罪。
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還是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行為。對于詐騙性質的傳銷則以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論處。當然,因為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因此這一界限也不明確。因此,司法實踐中存在某些定罪混亂的現象,也是在所難免的。
(三)實施傳銷行為,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
該司法解釋在《批復》的最后,還有一句話:“實施上述犯罪,同時構成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應該說,這句話在當時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其實,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規定。這一規定表明,在實施傳銷行為的時候,可能觸犯其他罪名,對此應當從一重罪處斷。那么,在實施傳銷行為的時候,會觸犯什么罪名呢?對此,在有關傳銷的法律規定中,其實已經有蛛絲馬跡。例如,《通知》第1條在論及禁止傳銷活動的根據時,指出:“不法分子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嚴重背離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利用傳銷吸收黨政機關干部、現役軍人、全日制在校學生等參與經商,嚴重破壞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利用傳銷進行價格欺詐、騙取錢財,推銷假冒偽劣產品、走私產品,牟取暴利,偷逃稅收,嚴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在此,《通知》提及傳銷行為可能觸犯的其他罪名,包括詐騙罪、銷售偽劣產品罪、走私罪、偷稅罪(現已改為逃稅罪)等。
傳銷行為在性質上的復雜性,也為此后的立法帶來一定的爭議。在《批復》頒布以后,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從事傳銷活動的行為,一般都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在少數情況下,涉及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1}(P.482)。而兩者區分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存在實際的經營活動。
案例I朱慶文等非法經營案{2}(P.220-233)
被告人朱慶文,男,1968年2月13日出生,廣西南寧市人,漢族。
2004年9月底,朱慶文與王愛云以廣西大順公司、順昌大順公司的名義,共同策劃,制定了“周周樂IC卡”發售計劃。朱慶文先后糾集、雇傭了被告人洪少彬等人參與實施該計劃。該計劃即以消費者直接向該公司購買螺旋藻、靈芝膠囊等保健品取得會員資格,后享受每周一次的高額返還營銷款,然后以消費者所購IC卡金額、份額多少將會員分為業務員、業務主管、加盟商,業務主管與業務員之間存在上下線關系,上線可從其發展的下線的營銷業績中按不同比例提成,享受津貼。“周周樂IC卡”分為三種,即面值360元的健康卡、面值1200元的金卡和面值3000元的白金卡。高額返款即消費者每購買一份健康卡,除可提取同等價值的保健品外,每周還可獲取返還的勞務費90元,17周內最高返款累計1500元;購買一份白金卡,除可直接提取同等價值的保健品外,每周還可獲取返還的勞務費249元,20周內最高返款累計4980元。
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朱慶文等人違反國家規定,合伙進行傳銷,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繳納費用,同時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進行非法經營,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已經構成非法經營罪。
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25條第(四)項、第25條第1款、第26條、第27條、第64條、第67條第1款、第7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的規定,判處被告人朱慶文有期徒刑13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00萬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分別判處2年零6個月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審判決以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
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審判決。
上述案例是刑法修正案(七)頒布之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對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一個典型案例。該案的“解說”(相當于裁判理由)在論及該案為什么定非法經營罪而不定詐騙罪或集資詐騙罪的依據時,指出:(1)該案傳銷行為存在貨物買賣行為,消費者可以用“周周樂IC卡”刷出保健產品,朱慶文在博白龍潭有螺旋藻生產基地,向綠冬公司購買保健產品。而詐騙一般沒有或者很少有貨物經營行為。(2)傳銷的利益主要依靠傳銷人自己層層發展下線來獲取,沒有下線就沒有利益。行為人陳述的周周樂IC卡推廣計劃的利潤來源,主要是建立在購卡者能在消費完原面額后仍繼續充值消費的基礎上產生,但這種假設是不現實的。詐騙則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承諾以定期利息、紅利等形式返還巨額利益相引誘。(3)報表、審計報告、賬戶清單和行為人供述、證人的證言可證實,行為人已經返還業務員大約幾千萬余元的本金及勞務費,可見確有返還大量勞務費,而詐騙返還的款項一般較小。以上對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傳銷行為與詐騙性犯罪的區分的論述,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當時《通知》所規范的是指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行為。這個意義上的傳銷行為,是一種法律所禁止的經營行為。在上述“解說”中,就明確地把傳銷界定為是一種未獲批準直銷經營許可的行為,指出:“傳銷,在國外又稱直銷,即指用傳遞方式進行銷售,一般是指企業不通過店鋪經營等流通環節,將產品或服務直接銷售、提供給消費者的一種營銷方式。”在此,“解說”把傳銷視為是直銷的營銷方式,朱慶文的大順公司所實施的傳銷行為之所以構成非法經營罪,是因為未獲得直銷經營許可。這一對傳銷行為的理解,把它與以傳銷為名所實施的各種詐騙犯罪加以區分。
然而,上述對傳銷的界定不僅與《意見(一)》關于傳銷的界定不同,而且與禁止傳銷條例關于傳銷的概念也不一致。禁止傳銷條例第7條所列舉的3種傳銷行為中,所謂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實則并無經營內容,只有團隊計酬具有經營內容。當然,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著拉人頭、收取入門費與團隊計酬競合的情形。
二、經營型傳銷抑或詐騙型傳銷:立法過程的逆轉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七)單獨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罪名之前,根據司法實踐的規定,對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行為(區別于以傳銷為名實施的詐騙犯罪)是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由此而解法律根據缺乏的一時之需。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司法實踐要求對傳銷行為專門設立罪名。我國學者指出:僅僅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傳銷和變相傳銷的性質加以規定,將傳銷行為納入非法經營罪的范疇,很難適應傳銷和變相傳銷的新特點,必須獨設非法傳銷罪,明確設定非法傳銷的刑罰{3}。對傳銷犯罪進行立法的建議得到立法機關的回應,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得以完成。
在刑法修正案(七)的制定過程中,對于傳銷犯罪如何設立罪名,存在爭議,并且前后發生了重大的變更。在2008年8月25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稿第4條中,對于傳銷犯罪是這樣規定的:在刑法第225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25條之一:“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犯罪行為的組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傳銷犯罪行為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這一規定是將傳銷犯罪的組織行為規定為犯罪,因此是一種組織罪。我國刑法中的組織行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共犯的組織行為,另一種是規定為正犯的組織行為。前者根據刑法總則的規定,以共犯論處,而并沒有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后者根據刑法分則的規定,以單獨犯罪論處。例如我國刑法第120條規定的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以及第294條規定的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而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稿對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罪的規定,就屬于以單獨犯罪論處的組織罪。值得注意的是,該草案還規定:“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這就是說,對于具體實施傳銷犯罪活動的,還是按照非法經營罪、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顯然也是參照刑法第120條和第294條第2款的規定。如此,則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的行為構成一個組織犯罪。如果該傳銷組織又從事傳銷活動的,則根據傳銷的性質又分別定罪:傳銷而具有經營內容的,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傳銷而具有詐騙或者集資詐騙性質的,以詐騙罪或者集資詐騙罪論處,并實行數罪并罰。
立法機關在論及這一規定的背景時,指出:“國務院法制辦、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提出,當前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方式組織傳銷的違法犯罪活動,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危害嚴重。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對這類案件主要是根據實施傳銷行為的不同情況,分別按照非法經營罪、詐騙罪、集資詐騙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為更有利打擊組織傳銷的犯罪。應當在刑法中對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組織的犯罪作出專門規定。經同有關部門研究,建議在刑法中增加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的犯罪。對實施這類犯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實行數罪并罰”。[1]因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上述規定是在原有司法解釋將傳銷行為納入非法經營罪規定的基礎上,對組織、領導傳銷組織行為的特別規定。
那么,這里傳銷組織的傳銷一詞如何理解呢?換言之,這里的傳銷是指具有經營內容的傳銷還是指以傳銷為名的詐騙?對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雖然并不明確,但草案有“傳銷犯罪行為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的專款規定,這里的行政法規包括前述《禁止傳銷條例》,而《禁止傳銷條例》明確把詐騙型傳銷和經營型傳銷都納入傳銷的范圍,因此,這是一種較為寬泛的傳銷概念。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上述規定,在法案審議中提出了一些意見,主要認為該罪的規定過于籠統,尤其是對傳銷行為按照行政法規確定,使該罪的構成要件呈現為空白狀態,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為此,2008年12月25日草案第2稿第4條中,對該罪的規定做了修改:在刑法第224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刑法修正案(七)最后定稿也采納了這一規定。從定稿的規定來看,不僅對傳銷活動進行了界定,更為重要的是將組織罪修改為詐騙性質的傳銷犯罪。并且,該條也從刑法第225條之一變更為刑法第224條之一。而刑法第224條是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從而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性質確定為詐騙犯罪。
如前所述,根據《禁止傳銷條例》7條對傳銷的列舉式規定,存在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和團隊計酬這三種傳銷方式。但在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關于傳銷的概念中,只規定了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的傳銷形式,恰恰沒有規定具有經營內容的團隊計酬的傳銷形式。至此,刑法修正案(七)關于傳銷犯罪的規定,在性質上發生了逆轉:從經營型傳銷改變為詐騙型傳銷。傳銷這個概念在我國刑法中的界定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傳銷本來是一種經營方式,就此而被我國刑法確定為一種詐騙方式。
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法教義學的考察
經過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正,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后,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頒布了《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二)》),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做了專門規定。對于上述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在理解與適用中存在以下需要研究的問題:
(一)罪名的推敲
在刑法修正案(七)通過以后,200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將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規定的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罪名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無疑,組織、領導是本罪的重要行為方式,但這一罪名概括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說是以偏概全。因為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表述句式是:組織、領導……,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在這一表述中,騙取財物雖然被包裹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這一句式之中,但它卻是對于本罪具有決定性的用語。在這種情況下,較為合理的罪名應該是傳銷詐騙罪。因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只是詐騙手段,其行為本身還是詐騙。
我們可以將刑法第224條之一與刑法第224條的規定相比,第224條是關于合同詐騙罪的規定。在這一規定中,立法機關也列舉了5種合同詐騙行為。但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并沒有以這5種行為確定罪名,而是以這5種行為的共同屬性——合同詐騙確定罪名。如果說,5種行為難以概括,因此不能以此為罪名。那么,我們比較刑法第194條第2款的規定:“使用偽造、變造的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他銀行結算憑證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對此,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并沒有根據罪狀,將罪名概括為使用偽造、變造的金融憑證罪,而是將罪名確定為金融憑證詐騙罪。因為使用偽造、變造的金融憑證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詐騙的特殊表現形態。刑法第224條之一也是如此,雖然條文主體內容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但基于該條文對于傳銷的內容界定,組織、領導這種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為主要特征的傳銷活動,其實就是一種詐騙的特殊類型。因此,以傳銷詐騙罪概括本罪的罪名,是最為確切的。在目前將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罪名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情況下,由于在罪名中沒有突出詐騙的性質,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傳銷并不必然是詐騙,因此傳銷詐騙一語似乎存在問題。但這里的傳銷詐騙是以傳銷為名所實施的詐騙,正如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詐騙一詞,合同與詐騙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里的合同詐騙,只不是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所實施的詐騙一語的簡稱而已。
(二)罪體的界定
根據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客觀上表現為組織、領導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為特征的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行為。
1.組織、領導
在刑法修正案(七)頒布之前的司法解釋中,將傳銷犯罪的行為表述為從事傳銷活動。這里的從事,是指實施。因此,對傳銷犯罪的行為界定得極為寬泛。刑法第224條之一則將行為表述為組織、領導,由此表明只有組織者和領導者的行為才構成犯罪,而一般傳銷活動的參與者則不構成犯罪。這一對行為的限縮,具有刑事政策的重大蘊含,體現了縮小打擊面的政策思想。既然是傳銷詐騙罪,那么,為什么參與傳銷活動的人員不構成本罪呢?對于一般的詐騙罪而言,只要參與詐騙活動的,無論是主犯還是從犯,都構成犯罪。但傳銷詐騙與之不同,只有這些傳銷詐騙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才是詐騙行為的實施者,而一般的參與者具有被引誘或者被脅迫的性質。雖然有些人也從傳銷中非法獲利,但從整體上說,這些參與者還是屬于被害人。正如在集資詐騙罪中,只有那些集資詐騙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構成犯罪,而一般的參與集資的人員,則屬于被害人。
根據前引《意見(二)》的規定,下列人員可以認定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的人員;在傳銷活動中承擔管理、協調等職責的人員;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曾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刑事處罰,或者1年以內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又直接或者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15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人員;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上述規定,雖然是以對組織者、領導者的列舉式規定的形式出現的,但其中包含了對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行為的描述。根據上述《意見(二)》的規定,傳銷活動中的組織行為是指傳銷活動中的發起、策劃、操縱行為;而領導行為是指傳銷活動中的管理、協調行為;以及傳銷活動中的宣傳、培訓行為等。
2.傳銷活動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前,當時在法律上對于傳銷的理解是存在混亂的。主要問題在于:法律上的傳銷是指經營型的傳銷還是指詐騙型的傳銷?顯然,在對傳銷行為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法律語境中,這里的傳銷只能是經營型的傳銷而非詐騙型的傳銷,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刑法第224條之一的罪狀中,立法機關已經對傳銷做了定義式的規定。按照該規定,傳銷包括兩種情形: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這就是所謂拉人頭;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這就是所謂收取入門費。在這兩種傳銷活動中,都沒有經營的內容,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銷。而是以傳銷為名,實際上是一種詐騙行為。
3.騙取財物
騙取財物是組織、領導傳銷罪的本質特征,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具有重要意義。關于騙取財物的行為,我國學者指出:“所謂騙取財物,是說由于傳銷行為屬于非法,所以通過傳銷活動取得的返利、報酬等任何財產,均屬于騙取財物。至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實際上是否騙取到了財物,不影響本罪的構成。也就是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不以騙取財物為必要。所以,‘騙取財物’屬于本罪可有可無的概念。”{4}(P.378)以上對于騙取財物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中的地位與意義的說法,我是不能茍同的。
首先,不是因為傳銷活動非法,所以通過傳銷活動取得的財產才屬于騙取的財物。而是因為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方法進行傳銷活動,其本身就屬于詐騙,因而其所取得的財物才是騙取的財物。
其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當然以騙取財物為其構成犯罪的要件。如果沒有騙取財物的,就不能構成本罪。當然,考慮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特殊性,本罪不以騙取的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是以發展傳銷人員的人數和層級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但這并不意味著騙取財物的數額對于本罪的定罪不重要。
再次,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來說,騙取財物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概念,而是不可或缺的內容。《意見(二)》對此也做了明文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飾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參與傳銷活動人員是否認為被騙,不影響騙取財物的認定。”而且,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性質,也是詐騙型傳銷與經營型傳銷的根本區分之所在。
在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法第224條之一中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詐騙財物與詐騙之間的關系,存在非同一性說的見解。這種觀點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騙取財物與詐騙不是同一性質的行為。例如,我國學者指出:
刑法修正案(七)第4條的規定中,雖然有“騙取財物”的特征表述,但傳銷活動“騙取”的含義,卻是推銷質差、價低等,冒充高質、高價位的“道具商品”或者“服務”,通過發展下線購買的人頭多少而獲取相應的高額回報。也就是說,傳銷不是以直銷產品或者實質性服務作為銷售者、推介者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而是以“拉人頭”的方式,賺取“人頭費”或高額“入會費”作為傳銷者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但這里的傳銷的道具商品仍然是商品,服務仍然是服務,只是不是其所描述的商品、服務而已,這是與詐騙非同一性質的行為。{5}(P.472)
這種觀點試圖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與詐騙加以區分,認為兩者并非同一種行為。筆者認為,這一理解是不妥的。以傳銷為手段的詐騙具有其特殊性,例如采取了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等方法,以此騙取財物,這是不可否認的。但以此特殊性而否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與詐騙具有同一性,這也是不可取的。
此外,張明楷教授則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騙取財物是對詐騙型傳銷組織(或者活動)的描述,亦即,只有當行為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具有“騙取財物”的性質時,才成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為顯示詐騙型傳銷組織(或活動)特征的“騙取財物”,不以客觀上已經騙取了他人財物為前提{6}(P.748)。這種觀點肯定采取拉人頭、收取入門費的手段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行為本身具有詐騙財物的性質,即承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詐騙財物與詐騙之間存在同一性,這是正確的。但這種觀點又考慮到刑法第224條之一所采取的“組織、領導拉人頭、收取入門費,騙取財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傳銷活動”這一表述,認為本罪的行為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并不是獨立的行為,只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這一行為的性質。筆者認為,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稿第4條將本罪的行為表述為“組織、領導實施傳銷犯罪行為的組織”,這是一種組織罪的立法表達。及至草案第2稿第4條修改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時候,仍然沿襲了先前的表述,沒有相應地改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而確定為“組織、領導以拉人頭、收取入門費作為形式,騙取財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傳銷活動”的罪狀。在此,騙取財物不是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相并列的行為要素,而是用來界定傳銷活動的形容用語。盡管如此,筆者認為還是要把本罪的構成要件概括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騙取財物。因此,騙取財物并不僅僅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行為的性質,而且是本罪獨立的客觀要素。因為詐騙犯罪在構成要件上具有其特殊性,不僅要有被告人的欺騙行為,而且包含了被害人因欺騙而產生認識錯誤,基于這種認識錯誤而交付財物的行為,這才是對詐騙型傳銷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完整表述。
在此涉及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詐騙罪和集資詐騙罪之間的關系。對此,張明楷教授一方面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騙取財物具有詐騙的性質;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認為刑法第224條之一與規定集資詐騙罪的第192條、規定普通詐騙罪的第266條是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關系,進而對以傳銷方式實施詐騙的案件適用特別法條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7}張明楷教授是以如果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對詐騙型傳銷只能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為理由,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詐騙罪和集資詐騙罪之間不是法條競合關系,而是想象競合關系,以便實行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但筆者認為,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在本體上存在區分,不能因為不同犯罪的法定刑輕重設置而混淆兩者之間的界限。更不贊同模糊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之間的界限的觀點{8}。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為傳銷詐騙罪,其與詐騙罪之間顯然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的競合關系。對此,只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盡管詐騙罪的法定最高刑高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至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的關系,則稍顯復雜。因為相對于詐騙罪而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都屬于特別法。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而言,不能認為存在特別法與普通法的法條競合關系,但可以認為存在交互競合關系。對此,可以按照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處理。
(三)罪責的界定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罪過形式是故意,這是沒有問題的。存在爭議的問題在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如何理解。對此,我國刑法學界存在非法牟利目的說與非法占有目的說之分。非法牟利目的說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是以牟利為目的。例如,我國學者指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為人明知自己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為法律所禁止,但卻通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達到騙取錢財,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1}(P.482)非法占有目的說則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例如我國學者指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并且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9}(P.686)”這里的騙取財物的目的完全可以理解為非法占有的目的。當然,這里沒有明確地采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提法,也還是反映出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某種猶豫和踟躕態度。
在以上兩種觀點中,非法牟利說是通說。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牟利目的與營利目的并無區分。在大多數罪狀中,立法者都采用了以營利為目的的表述,只有個別犯罪稱以牟利為目的。無論是以營利為目的還是以牟利為目的,其前提是存在經營行為。因此,這種把以牟利為目的確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主觀違法要素的觀點,與對本罪的傳銷行為是否具有經營性的理解存在直接的關聯性。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本罪之前,對于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傳銷犯罪,將其主觀違法要素確定為以牟利為目的或者以營利為目的,都是正確的。但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傳銷活動是詐騙型傳銷的情況下,仍然承襲以牟利為目的的表述,就存在問題。筆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屬于傳銷詐騙罪,是詐騙罪的特殊法。因此,對于本罪的主觀違法要素,應該表述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四)罪量的界定
刑法第224條之一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沒有規定罪量要素,但并非只要實施了這種傳銷詐騙行為,就一概構成犯罪。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二)》(以下簡稱《追訴標準》)第78條規定:“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根據這一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只有達到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規模,才能構成本罪。
案例II程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10}(P.61-63)
2012年5月底至6月初,被告人程某在博愛縣打著“山東陽光電子商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陽光公司)”的旗號,在被告人郝某的幫助下,在博愛縣清化鎮重陽路以其妻子王愛利的名義設立報單中心,推銷該公司無任何使用價值的電子幣,以繳納一定費用購買電子幣獲得加入資格,成為陽光公司的會員,并按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和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進行傳銷活動。
該傳銷活動經營模式為:每單1000元對應購買陽光公司1000電子幣,每人最多購買8單,獲得加入資格成為會員,每天按營銷計劃獲得返利。會員每發展1名人員加入,可獲得獎勵100元。成為繳納2000元購買2000電子幣可單獨設立報單中心,設立報單中心后,每向陽光公司報1單業務可獲得報單費30元。
截至案發,程某共計直接或間接發展人員96人且層級達9級,涉案金額481000元。被告人程某非法所得14400元,被告人郝某非法所得9620元。案發后,被告人程某退交非法所得4980元。
對于本案,博愛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程某、郝某組織、領導以推銷電子幣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購買電子幣的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且直接或者間接發展人員96人層級達9級,其行為均已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告人程某、郝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
博愛縣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1條之一、第67條第3款、第64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一、被告人程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
二、被告人郝某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
三、對被告人程某退交的非法所得4980元,予以沒收。對被告人程某非法所得的9420元,被告人郝某非法所得的9620元,予以追繳。
對于本案的定性,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程某、郝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并使他人陷入認識錯誤,因他人基于認識錯誤而自愿處分財產,行為人獲取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所以程某、郝某構成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陳某、郝某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其行為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應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以上兩種意見顯然是按照詐騙罪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不同構成要件分別對本案事實進行了描述:詐騙罪的意見是按照行為的本質進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形成了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認識錯誤,因他人基于認識錯誤而自愿處分財產,行為人獲取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這樣一幅詐騙罪的犯罪圖景。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意見則是按照行為的表面運作進行寫真式的敘述,形成了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匯總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這樣一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犯罪輪廓。其實,以上兩種理論敘述是對同一種行為的不同角度的表達,兩者之間存在表象與本質之間的表里關系。因此,詐騙罪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客觀上是競合的。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究竟如何界定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間的關系,以便正確地對兩罪加以區分呢?對此,該案的“法官后語”指出:
出現以上兩種意見,其主要原因在于對騙取財物的不同理解。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區分的關鍵點在于主觀方面:詐騙罪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行為人主觀上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是具有非法牟利的動機。在傳銷活動中,為了不斷發展人員加入,行為人通常用高額利潤做誘餌,夸大或虛構傭金或獎金收入,收取高額入門費或強制購買產品,這似乎具有某些詐騙罪的特征,但傳銷中參加者是為追逐高額回報而加入其中,其決定交易是受到利益誘惑,而不是因虛構事實、行為誤導而導致產生錯誤認識,故其行為不是受害人行為,不受法律保護。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組織者和領導者才構成本罪,一般參加者不構成犯罪{10}(P.63)。
對于程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博愛縣人民法院的定性是完全正確的。但“法官后語”對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間關系的論述則難以成立。
這里主要還是涉及對本罪的主觀違法要素的理解:到底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還是與非法牟利為目的?本案法官否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主張以牟利為目的。正如前文所言,非法占有目的和非法牟利目的的根本區分在于:客觀上是否具有營利行為。如果是營利型的傳銷行為,主觀上當然具有營利目的。反之,如果說詐騙型的傳銷行為,則主觀上不可能具有營利目的。基于詐騙行為,主觀上只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程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已經認定被告人是以推銷電子幣的經營活動為名,采用傳銷方式,騙取他人財物。在這種情況下,主觀上怎么可能具有牟利目的而不是占有目的呢?
(五)團隊計酬的定性
團隊計酬是傳銷的一種方式,被稱為經營型的傳銷行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傳銷活動的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
關于團隊計酬到底是直銷還是傳銷的問題,在我國法律上始終是存在模糊的。在刑法修正案(七)頒布之前,無論是在《意見(一)》還是在《禁止傳銷條例》中,都是將團隊計酬納入傳銷的范疇。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則將這種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但刑法理論上,也有些學者將團隊計酬歸入直銷的范疇,認為這是直銷活動中的多層次計酬。我國學者在論及拉人頭和團隊計酬的區分時,指出:
雖然二者都采用多層次計酬的方式,但是仍有很大不同:一是從是否繳納入門費上看,多層次計酬的銷售人員在獲取從業資格時沒有被要求繳納高額入門費,而拉人頭傳銷不繳納高額入門費,或者購買與高額入門費等價的“道具商品”是根本得不到入門資格的;二是從經營對象上看,多層次計酬是以銷售產品為導向,商品定價基本合理,而且還有退貨保障。而拉人頭傳銷根本沒有產品銷售,或者只是以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的“道具商品”為幌子,且不許退貨,主要是以發展“下線”人數為主要目的;三是從人員的收入來源上,多層次計酬主要根據從業人員的銷售業績和獎金,而拉人頭傳銷主要取決于發展的“下線”人數多少和新入會成員的高額入門費;四是從組織存在和維系的條件看,多層次計酬直銷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取決于產品銷售業績和利潤。而拉人頭騙取傳銷組織則直接取決于是否有新成員以一定倍率不斷加入{11}。
依筆者之見,團隊計酬仍然屬于傳銷而非直銷。至于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則根本不是傳銷,而是以傳銷為名所實施的詐騙行為。因此,如果把團隊計酬從傳銷中抽離,傳銷這個概念就不復存在了。更何況,直銷是法律所允許的,而團隊計酬式的傳銷則為法律所禁止。
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將傳銷界定為拉人頭和收取入門費以后,團隊計酬的傳銷形式沒有包含在本罪的構成要件之中。對此,我國學者一般都認為,對于這種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仍然應當以非法經營罪論處。例如,張明楷教授指出:“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由于組織、領導原始型傳銷活動的行為,并不具備刑法第224條之一所要求的‘騙取財物’的要素,不能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又由于這種經營行為被法律所禁止,并且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依然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7}應該說,這一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事實上,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之前,司法實踐中對這種經營型的傳銷行為本來就是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的。在刑法修正案(七)未對這種經營型的傳銷行為進行規定的情況下,為懲治這種傳銷行為,對其按照非法經營罪論處是完全正確的。然而,2013年11月14日《意見(二)》對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的定性問題做了以下規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與此同時還規定:“形式上采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于‘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241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將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做了非犯罪化的處理。可以說,這是對傳銷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重大調整。以下將討論的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就十分真實地反映了在司法實踐中,這種刑事政策的調整對具體案件處理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當事人命運的逆轉。
案例III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12}(P.63-68)
被告人曾國堅,男,1974年10月17日出生,漢族,無業。2010年1月15日因本案被逮捕。
(其他被告人略)
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犯非法經營罪,向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9年6月始,被告人曾國堅租賃深圳市羅湖區怡泰大廈A座3205房為臨時經營場所,以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發展經銷商的名義發展下線,以高額回饋為誘餌,向他人推廣傳銷產品、宣講傳銷獎金制度。同時,曾國堅組織策劃傳銷,誘騙他人加入,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入會費用,取得加入和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并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以下線的發展成員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均在上述場所參加傳銷培訓,并積極發展下線,代理下線或者將下線直接帶到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繳費入會,進行交易,形成傳銷網絡:其中曾國堅發展的下線人員有鄭某妮、楊某湘、王某軍、楊某芳、袁某霞等人,楊某芳向曾國堅的上線曾某茹交納人民幣(以下未標明的幣種均為人民幣)20000元,袁某霞先后向曾國堅、曾某茹及曾國堅的哥哥曾某建共交納62000元;黃水娣發展羅玲曉、莫紅珍和龔某玲為下線,羅玲曉、莫紅珍及龔某玲分別向其購買了港幣5000元的產品;羅玲曉發展黃某梅為下線,黃某梅發展王某華為下線,黃某梅、王某華分別向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交納入會費港幣67648元;莫紅珍發展龍某玉為下線,龍某玉發展鐘某仙為下線,鐘某仙發展周某花為下線,其中龍某玉向莫紅珍購買了港幣5000元的產品,鐘某仙、周某花分別向亮碧思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交納人會費港幣67648元。2009年12月8日,接群眾舉報,公安機關聯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羅湖分局將正在羅湖區怡泰大廈A座3205房活動的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等人查獲。
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均構成非法經營罪,且屬于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曾國堅積極實施犯罪,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均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且犯罪情節輕微,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依法均可以免除處罰。曾國堅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對其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5條、第25條第1款、第26條、第27條、第72條之規定,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曾國堅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并處罰金1000元;以非法經營罪分別判處被告人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免予刑事處罰。
宣判后,被告人曾國堅不服,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并基于以下理由請求改判無罪:亮碧思(香港)有限公司有真實的商品經營活動,其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也沒有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曾國堅與原審被告人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行為,而不應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鑒于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的行為已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故其行為不應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曾國堅的上訴理由成立。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25條第1款第(二)之規定,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撤銷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2011)深羅法刑一重字第1號刑事判決;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無罪。
上述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從法院認定的傳銷事實來看,屬于團隊計酬的形式。因此,公訴機關對于本案是以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的。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對于本案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之后,對傳銷活動的刑法評價應當實行單軌制,即僅以是否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特征進行評價,如果不符合該罪構成特征,就應當宣告無罪,而不能再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則主張雙軌制,認為刑法修正案(七)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并未明確取消非法經營罪的適用,對于傳銷活動,即使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特征,也仍然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在以上兩種意見中,法院最終采納了一種意見,宣告被告人無罪。在以上爭論中,提及所謂單軌制和雙軌制的概念。單軌制是指對于傳銷行為只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處理,這也就暗含了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團隊計酬不構成犯罪的意思。而雙軌制則認為,對傳銷行為如果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應以該罪論處。不符合該罪特征的團隊計酬傳銷行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因此,這是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設立以后,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究竟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所存在的爭議。
顯然,對于本案作出無罪判決是完全正確的。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本案提出的法律適用問題并不是“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設立以后,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究竟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而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尚未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立案追訴標準,但經營數額或者違法所得數額達到非法經營罪立案追訴標準的,能否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在這一敘述中,就隱含著本案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的傳銷行為,如果發展人數和層級達到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立案追訴標準,是可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論處的意思。因此,這里存在著對法律適用問題提煉上的偏差。
在本案裁判理由中,作者論述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包括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團隊計酬按照有關司法實踐不再以犯罪論處,指出:
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條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客觀行為中未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活動,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傳銷活動如何定性,存在一定爭議。鑒于此種情況,意見(二)對“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進行了專門規定。《意見(二)》第五條第一款對“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的概念進行了明確。該款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傳銷活動的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意見(二)》第五條第二款對“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的定性進行了規定。該款規定:“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形式上采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于‘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依照刑法第224條之一的規定,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12}(P.67-68)。
顯然,這段話并不是在審理本案當時的意見。因為當時對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不以犯罪論處的司法解釋還沒有頒布。試想,如果當時司法解釋已經頒布,對此還會存在爭議嗎?
與此同時,裁判理由又認定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的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指出:“在本案中,曾國堅等人實施了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傳銷行為。客觀上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特征。只是依照《追訴標準》的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起點為‘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而現有證據顯示本案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不足三十人。”{12}(P.67)因此,本案只是沒有達到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而已。如果已經達到追訴標準,是完全可以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
顯然,本案裁判理由的上述兩個方面的論述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案件材料反映,在一審階段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曾建議羅湖區人民檢察院就傳銷人員的人數和層級進行補充偵查。羅湖區人民檢察院復函認為刑法修正案(七)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了規定,但未取消非法經營罪的適用,根據刑法第225條第四項及《批復》的規定,曾國堅等人的行為即使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也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特征,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沒有補充偵查必要。因此,即使是檢察機關也認為,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不是是否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的問題,而是在刑法修正案(七)設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以后,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還是否可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問題。
之所以出現以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情況,事實上是該案的敘述省略了時間維度有關。因為從該案材料中,我們看不到具體的審理時間。只是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的本案的案號中可以確定這是2011年受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批復是2012年。而規定團隊計酬不以犯罪論處的司法解釋是2013年11月14日頒布的。在這一司法解釋頒布之前,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是否以非法經營罪論處,法律界限并不明確,而且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對本案以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就是十分正常的。而一審判決對被告人曾國堅等人也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作出了有罪判決。第一次上訴以后,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發回重審。重一審判決仍然認定被告人曾國堅等人構成非法經營罪。再次上訴以后,對于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逐級層報請示,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刑他字第56號批復明確:“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如未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追訴標準,行為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亦不宜再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據此,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不足30人,亦沒有相應證據證明該傳銷體系的層級在三級以上,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改判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無罪。
在筆者看來,曾國堅案真實地反映了在關于團隊計酬的傳銷行為不以犯罪論處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團隊計酬的傳銷案件如何處理問題上的一定程度的混亂。只是在司法解釋正式出臺以后,對于這個問題的法律界限才得以明確。但問題在于,刑法修正案(七)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法,本來是要加強對傳銷活動的懲治。但立法過程的一波三折,司法解釋的限縮性規定,刑法對于傳銷活動的打擊力度不是加強而是弱化了。
這是立法者所愿意看到的嗎?不得而知。
(責任編輯 于賀清)
【注釋】 作者簡介:陳興良,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興發巖梅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1]李適時: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說明。
【參考文獻】 {1}周道鸞、張軍主編:《刑法罪名精釋》(第4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2}國家法官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編:《中國審判案例要覽》(2008年刑事審判案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熊英:“對設立非法傳銷罪的立法思考”,載《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4年第12期。
{4}曲新久:《刑法學》(第2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5}馬克昌主編:《百罪通論》(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6}張明楷:《刑法學》(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7}張明楷:“傳銷犯罪的基本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9期。
{8}張明楷:“犯罪之間的界限與競合”,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
{9}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第5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10}國家法官學院案例開發研究中心編:《中國法院2015年度案例(刑法分則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11}黃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讀”,載《人民檢察》2009年第6期。
{1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編:《刑事審判參考》第92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還有70%,馬上登錄可查看